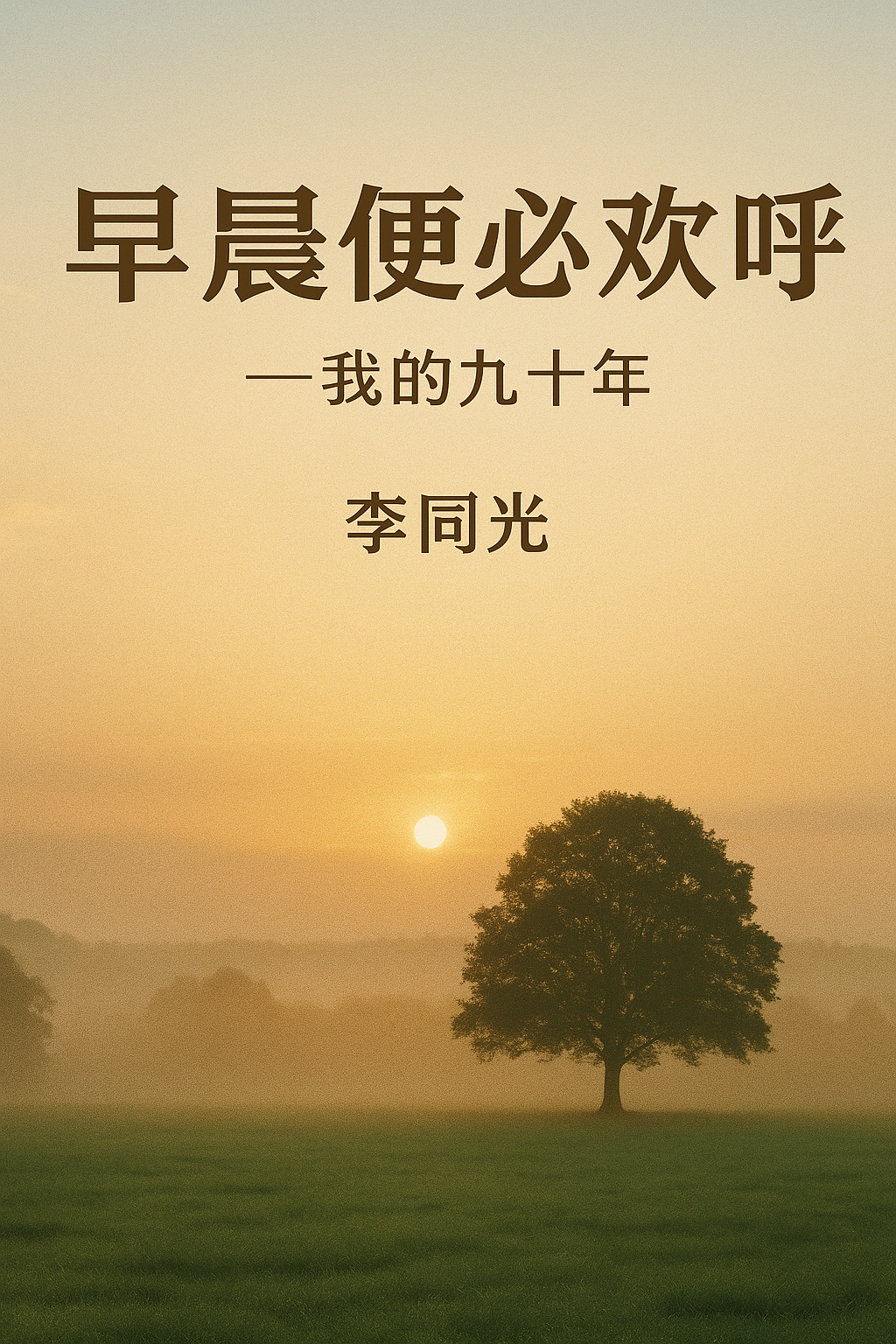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汲县看守所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命记》33:25)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言》24:10)
走进高墙林立的汲县看守所大院,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小道,我来到汲县看守所的办公室。押我进来的那个武装公安,给我松了手铐,取走了我的眼镜、裤带、以及口袋中的几张粮票和数十元人民币。
在沉默中,他领我走进一个空荡荡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由四座房屋围合而成,那个公安用一把蛮大的钥匙打开了用粗大铁链锁着的门。门内黑洞洞的,虽然看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我“入号”了!
那是一间昏暗的牢房,沿着墙壁,是用砖砌成的一排“土炕”,炕上挤着黑黝黝的二十来个人,没有人出声。
狱规不准彼此打听案情,但几天之后,我就知道这间牢房关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小偷以及流窜犯等等。
“流窜犯”又称“盲流”,并非一定是真正的犯罪分子。这种特殊流民,是1958年“大跃进”导致农村经济凋零的产物。饥饿的农民们为了寻找可以混口饭吃的地方,就爬上火车,并无一定去向,只是随外流荡,但若碰上列车乘警查票,他们就会被送到“收容所”,然后“劳动教养”,罪名是“影响社会治安”。
牢房的天花板很高,顶上一盏昏暗的电灯不分日夜,照着这间初秋阴冷的牢房。透过墙上一个格子铁窗,照进来一丝光线,使我无限渴望外面的自由世界。
透过铁窗,我注意到窗外房顶高处有一个戒备森严的武装哨所,哨所下面站着另一个持枪的警卫,他用冰冷的目光监视着牢房里的一举一动。
在这间牢房里,我很快染上了虱子。虱子的繁殖力极强,是一些像白芝麻般大小的寄生虫,它们成串结队地钻到我贴身衣裤的褶缝中。
夜晚,我和犯人们挤在炕上,我最大的“享受”就是抓挠虱子吸血引起的浑身瘙痒,因为那种痒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钻心奇痒。
看守所是从不供应水的。每人每天吃两顿高粱米熬成的粥,河南人称其为“糊涂”,每顿两大碗。因为既无水洗碗,又无筷子、勺子可用,所以碗底总会积着一层上一顿被人舔过以后残留下来的高粱米碎渣。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我只能用这样的碗喝粥。我和所有囚徒一样,很快就喝完我的高粱米“糊涂”。
每天黎明即起,犯人们排队入厕,解决大小便问题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并且绝无手纸可用。
然后,两个人一前一后,把粪桶抬到牢房外面。
紧接着,我和二十来个犯人排成一个长队,前后都有武装警卫押着,先“报数”、“点名”,然后抬着粪桶,走十来里路到城外的地里劳动。饮水及中午的高粱米“糊涂”都是看守所的人送来的,但是绝无洗手的水。
多年之后,一位同事的母亲告诉我说,当年她十二岁的小儿子有一天从外面跑进屋,哭着对她说:“我看见李大夫了。他和其他犯人在城外‘刨地’。李大夫被弄成那样了。呜……”
天黑收工。夜幕下,我们这群疲惫不堪、饥寒交迫被囚的人犯,在前后都有武装警卫押送下,抬着倒空的粪桶,或扛着农具,步履蹒跚,艰难地走回看守所。在那个被血雨腥风冲击着的社会中,囚徒们被世人羞辱,被蔑视,真的成了一台戏;街道两旁,看热闹的小孩子们手舞足蹈,不时发出喊叫声:“劳改犯!”“快来看,劳改犯!”我们无言以对,只有低着头,如同幽灵一般,默默地回到看守所。
我日夜不停地思念着母亲。按照预定的日子,她应该已经到达汲县了。每晚收工回来,我总是幻想着,似乎看见她矮矮的身影站在灰暗的街灯下等着我。但是她没有出现。妈妈呀,您究竟在哪里?难道迎接您的,只有中原大地上秋风的哀号吗?!您为什么还没有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心急如焚,万分焦灼,不敢再细想下去了。
有一天,我在重重的煎熬中终于鼓足勇气,向牢房格子铁窗外的武装警卫喊了一声:“报告班长!”“干啥?”
我向他陈述了那些困扰着我、令我揪心的顾虑。没想到他和气地对我说:“如果你妈来了,看守所会按党的‘革命人道主义’原则,让你们母子见面的。”
可是,母亲始终没有出现在我眼前。这是为什么呢?我一直等候并苦思冥想的这个“为什么”,直到两个年头以后才得到答案。
三周后的一个清晨,我在牢房中被看守人员叫起。遵照他的吩咐,我收拾好自己简陋的行装,背着被褥,又来到看守所办公室。
一个身着军装的干部很和气地对我说,他要送我去新乡,临行前还加了一句:“不上铐。”
我们走出看守所大院,外面刚下过雨,地面很潮湿。我被关了三个星期,因为没有水可以清洗,身上很脏,还长了虱子。我的手背皮肤红肿,并且开始溃烂。
我的经历告诉我,一个人对外界生活条件的好坏有很强的可塑性,但是我在汲县看守所的恶劣条件下,虽然只被关了三星期,但是营养不良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使我十分虚弱。我感到精疲力竭,身心交瘁,实在没有力气再扛这不到三十斤重的被褥了。
这位穿着军服的干部,见我艰难地扛着被褥、摇摇晃晃要摔倒的样子,对我说可以雇一辆三轮车,把被褥送到火车站托运,但要我自己出钱。我对他的照顾非常感谢,因为走到车站要四十分钟,而我实在没有力气去扛自己的被褥。
火车很快抵达新乡站。那位穿军装的干部取了我托运的被褥,又叫了一辆三轮车,放上我的被褥。他对三轮车工人说:“新乡机械厂。”我们在车旁跟着,离开车站走了不远就到那个工厂门口。我抬起头来,看见大门一侧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竖写着“河南省第二监狱”几个大字,赫然跃入我的眼帘,令我胆战心惊!
监狱高高的围墙上面,绕着几道铁丝网,清楚标明这是“高压电网”。我心里向主惊呼说:“主啊!这是监狱啊!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对我的处理决定是最高行政处分‘劳动教养’,但是进监狱则是更严重的处罚,是刑事处分,是罪犯接受‘劳动改造’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