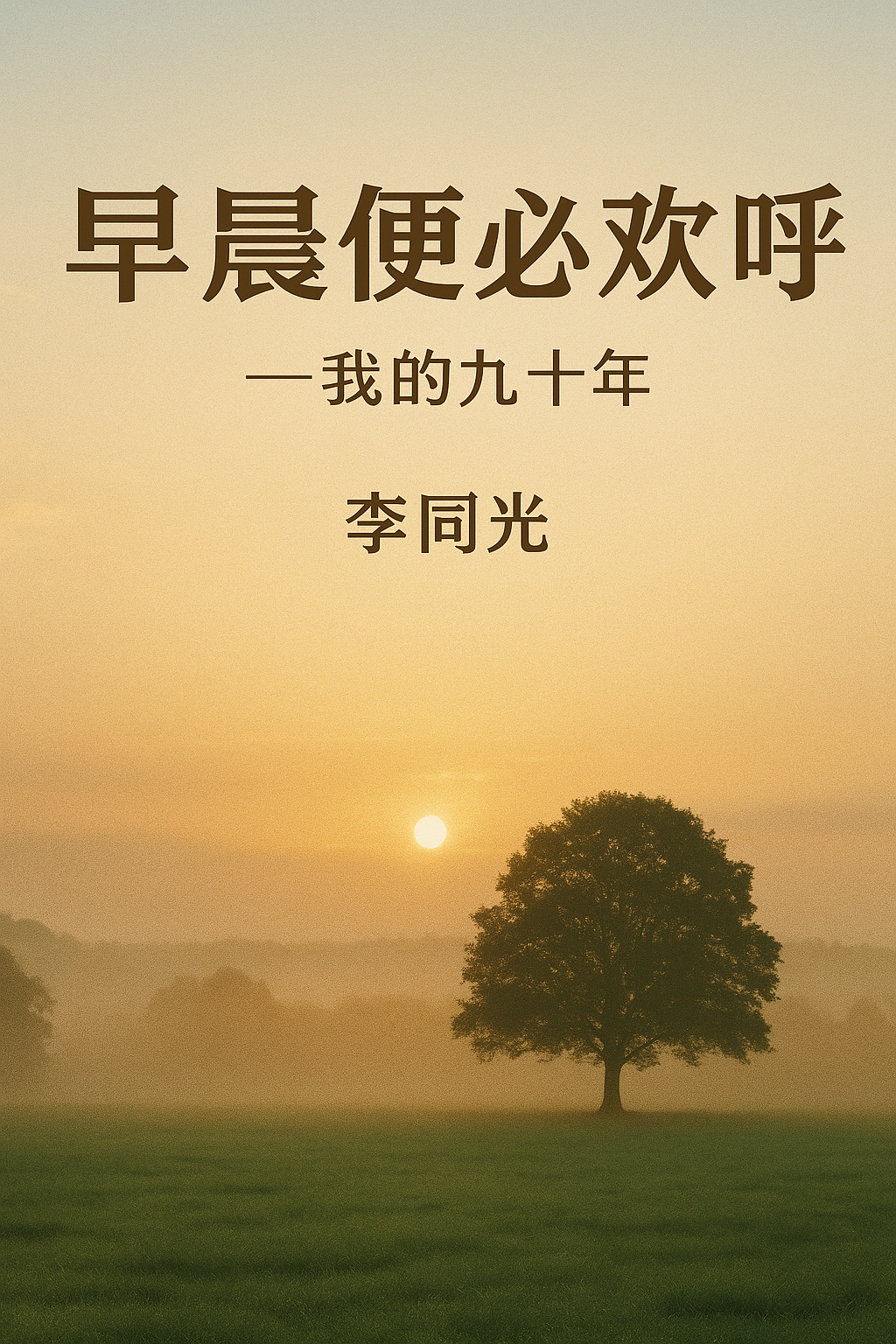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9·28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1:29)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诗篇》39:9)
1960年9月28日,礼拜四,是我终生不忘的日子。
三天后就是国庆节。日子过的既慢又快,“右派分子”这顶无比沉重的“帽子”压在我头上已经两年了。
早在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党中央分期分批给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帽”的决定。我朝思暮想,天天渴望着“摘帽”的日子也会临到我,但理智更告诉我,这个日子离我越来越远了。因为1960年夏,我的圣经成为我“抗拒改造”的“证据”。
保卫科科长嘴有点歪,眼睛有点斜,据说原来是河南汲县的公安局长。他要求“右派分子”们互相监督,凡检举揭发坏人坏事者,还可以立功赎罪。
有一个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新乡专区医学院职工,下放农村劳动三年后刚刚回来,和我住同一寝室,他不失时机,积极检举揭发我有四项罪行:其一,我说“双腿乏力,常有饥饿感”;其二,给学生们讲解原发性高血压病因时,我说“这和长期精神紧张有关”,并引证苏联高等院校病理解剖学中提到二战时,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三年,城内居民高血压发病率明显上升;其三,看到学校“民兵训练”时,我说“他们用的步枪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用过的旧枪,而现代战争要用新式武器才行”;最后,更为严重的是,我桌上一直放着一本圣经!
无端灾祸从他口出一出,立刻我就又加增了四个新罪名:一是“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二是“散布战争恐怖论”;三是“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全民皆兵’的政策”;四是“天天还看圣经,相信基督教,不好好改造思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为此,从1960年5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我被“批斗”。
可是此后不久,我又一下子被搁在一边,仿佛我这个人不存在似的。保卫科也未再叫我去“交代”什么。但我仍是忧心忡忡,难道对我就此善罢甘休了吗?迷蒙中,虽然我总感到“祸在旦夕”,但不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将要来临。
我日以继夜思念着母亲和弟弟妹妹们。1957年以来,我们已经三个年头没见面了。正好国庆节将临,我和母亲在信上说好,她将在1960年9月30日从上海来看我,同行的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邬妈妈。
多年来,邬妈妈和我的母亲都是上海虹口灵粮堂的执事。她的女儿锦文姊妹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在河南安阳市卫生防疫站工作。和我一样,她也戴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
从我所在的汲县(今卫辉市)往北,就是安阳。因此,两位思念儿女十分心切的母亲约好结伴同行。
就在那一天,1960年9月28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还飘着微微细雨;刺耳的高音喇叭声震醒了我。原来是广播一个紧急通知:“今天早上七点钟在大礼堂召开重要会议,全院职工务必准时参加。”“右派分子”是从来没有资格参加职工大会的。我纳闷这会是什么重要会议要这么早召开呢?
我们十来个“右派分子”和往常一样,每天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打扫厕所。厕所里积累了许多被秋风吹进的枯黄树叶,当我正努力地清扫这些成堆的落叶时,右派组长满脸紧张地从外面跑进来,叫我们立即去大礼堂参加职工大会。这时,我的心更纳闷了,且伴随着一种不祥之感。
待我走到大礼堂前面,有一个人在门口等着我,叫我交出办公室钥匙。我心里犯嘀咕:“这是为什么?”
大礼堂已经坐满了人,却没有平时开会前的那种喧哗声,连呼吸空气似乎也很沉重。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十几个“右派分子”被人领到一排空位子上坐下。我的左右两侧,都有人把我挤得紧紧的。
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中,我猛然觉得这个重要的紧急职工大会可能与我有关,却又不晓得到底有什么关系。
接着,党委秘书站在话筒前宣告:“今天这个大会是宣布重新处理右派分子李同光的大会!”话音未落,有人厉声高喊:“右派分子李同光站到前面去!”我听得出来,此人是解剖教研组的一个身为共产党员的实验员。顿时,已经半麻木的我,依顺地走到礼堂的最前面,低头面对群众,木然而立。
我又听到党委秘书宣布我的罪状是:“坚持唯心主义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经上级批准,判处劳动教养!”他的话音未了,台上突然下来一个身穿警服、右手拿着手枪的公安,他立即给我戴上手铐,将我押出会场。
我先被带到学校行政楼上的保卫科。那个歪嘴的科长瞠着他那双斜眼,坐在办公桌旁,厉声对我喝道:“蹲下!”
接着,他给我看了新乡地区公安处对我的处理决定,上面写着:“最高行政处分、劳动教养……”。
他居高临下,又对我说:“这是对你的宽大处理,否则应该判你劳改。你有啥要说的?”我蹲在地上,低着头,怯声回答说:“只有一个请求。”“说!”“我妈要从上海来看我,就这两天会到。我存折上还有几十块钱,请求领导给她发一个加急电报,叫她不要来。她年老体弱,还有高血压。”我听得非常清楚,这个科长对我唯一乞求的回答只有两个冷酷的字:“不行!”
离开保卫科,我被押回我曾经的寝室。有人将我的被褥从铺着稻草的床上掀起,对角打结,再套在我的脖子上。
那个斜眼的保卫科长对我说的最后一句狠话是:“放老实点!”就这样,我在1960年9月28日,走出了新乡专区医学院的大门。
早晨七点多钟,路上还少见人影。在朦胧的晨雾中,我背着自己的被褥,胸前是铐在一起的双手,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塑料套鞋,是两个月前母亲托人从上海带给我的。
那个枪不离手的公安在后面押着我,随着他厉声的“左拐”、“右拐”的命令,我低着头往前行,但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方。
我心乱如麻,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我在心中默默地对主说:“主啊!难道这就是你要我走的十架道路吗?”
我似乎听到一个优美而又坚定的旋律:“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要放一切在死的祭坛上面,火才在这里显现……”。
1953年前后,我每逢寒暑假参加上海市大专院校基督徒学生聚会时,弟兄姊妹们常常唱这首歌;副歌中有一句富有挑战性的歌词:“这是十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背十架为你主?”每次唱到这里,弟兄姊妹们都会热泪盈眶。我低着头一边走,一边想着这首歌。
两千年前在耶路撒冷古城,主耶稣伤痕累累的身体,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各各他,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我此刻身上既无鞭伤,所背的也只是自己的被褥,我要去的地方,肯定不是各各他;我怎么可以如此比较呢?我配吗?
我又突然想到保罗的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罗马书》8:35-39)。在上一医基督徒团契聚会中,我们常常念这段经文,并且反复咏唱。
我对主说:“主啊!尽管我现在没有自由,双手被铐,也不晓得前面还会有什么苦难,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与你的爱隔绝,因为你以永远的爱爱我!除你以外,我一无所有。”
我这样东想西想,可是想的最多、也最使我揪心的则是:“母亲来了怎么办?”
我曾在信中告诉她,因为要天天劳动,我不能到火车站去接她,但我会把寝室的门钥匙交给传达室,她可去取。我也会把两个暖水瓶都灌满热水,她可以先洗洗脸,等我结束劳动就回来看她。
我又想到,今天发生的事情太突然了,虽然半年来我一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不祥预感,却绝没想到我真会被突然戴上手铐,立即押走。措手不及中,我哀求保卫科长代发加紧电报,叫母亲不要来,结果也同样被他冷酷拒绝。
很有可能,母亲此刻已经在来汲县的路上了。
我的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悲戚的画面:慈母年迈,望子心切,以带病之躯,千里迢迢来看望未见面达三年之久的长子。如果再过两天,9月30日她按时到达,而她久别的儿子却已戴上手铐,押送“劳动教养”了!
这样突然袭来的残酷打击,谁能承受啊!妈妈真来了,又有谁会怜悯、接待这位“阶级敌人”的老母亲呢?她患有多年的高血压……。想到这里,我心如刀绞,怆然涕下……那时,我仿佛身陷浓密的大雾之中,迷失在天地间,也辨不清东西南北;我内心深处始终挂念着三年未见的母亲。
八天以后,是我26岁生日。往年,每到这一天,妈妈一定寄来祝我生日快乐的信。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心中向我的神呼求:“神啊!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押我去的目的地是“汲县公安局看守所”!我的常识告诉我,看守所是犯人被捕后、尚未受审及判刑的临时羁押之地。我并非犯人,怎么会送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