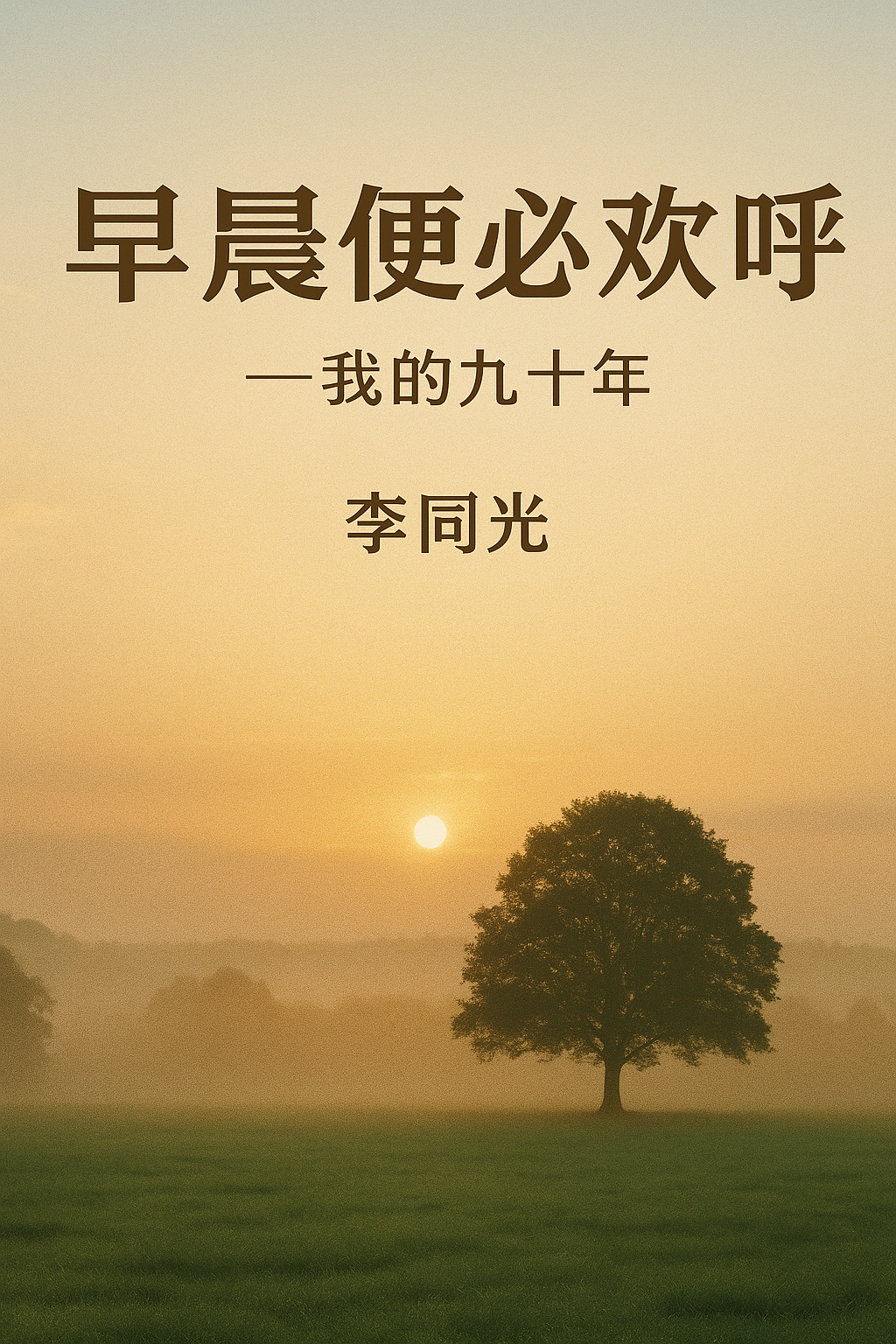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二章
第二章
我的母亲
“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申命记》31:6)
先母丁崇文(1911-2003),出生于上海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自幼便学习读经祷告。外婆丁葛菊英(1878-1967),原籍镇江丹徒区辛豊镇。其父曾是洪秀全麾下的“太平军”人。外婆早年就学于崇实女中,该校是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的父母在镇江宝塔山创办的。赛珍珠于1938年因她用中国题材写成的长篇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父母都是长老会宣教士。后来,外婆毕业后留校,成为崇实女中的数学老师。清朝末年,她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还会说、写、听、读英语。外婆具备的文化、教育和学识等多方面的素质及其修养,在她那个时代,或是在她以后的时期,都是十分罕见的。我还记得外婆每天早晨起床后,先读圣经,然后跪在床前祷告,天天如此。
1931年,先母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系,念大二时和父亲成婚。此后,她一直是家庭妇女,一辈子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
我有两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八年抗战(1937-1945),我们在山城重庆,抗战胜利后到南京(1945-1948),每人成长的岁月都是在母亲用诵读圣经、吟唱赞美诗,和跪在天父面前的祷告中度过的。
1948年秋,父亲的晚期胃癌广泛扩散。医生对母亲说,父亲的生命只有半年左右。1948年12月下旬,应大姨和姨夫邀请,我们全家离开南京来到上海,住在他们家中。
1949年1月20日,我们搬进了母亲刚买下的房子,那时父亲病况已经危重。1月24日晚,母亲独自跪在父亲的病床前,流着眼泪,苦苦哀求天上的父神施行神迹,医治父亲像医治希西家王那样(《列王纪下》20:5-7),并增加父亲的寿数。可是,母亲深感这样的倾心祷告,灵里不通。天上的父神用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马太福音》26:36-46),启示母亲顺从圣灵的带领,要顺服神的意念。于是,母亲再次祷告说:“主啊!我顺服,愿你的旨意成全”。
祷告不长,但她突然感到心里平安,喜乐满溢,眼泪止住,重担也脱落了,甚至觉得自己好像腾空飞起。这种超自然的喜乐,绝不能用人的理智去理解,因为母亲以客西马尼园中的耶稣基督为榜样,在极度忧伤悲痛中,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包括情感、心思和意志都完全降服在神面前。正如保罗所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帖撒罗尼迦前书》1:6)。
很奇妙的是,也就在那个特殊时刻,父亲睁开眼睛,轻声对跪在床前的母亲说:“我听见你刚才的祷告。我也顺服天父的旨意。你睡一会儿吧。”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后说的一句话。母亲一夜未合眼,一直守在父亲身边。
第二天是1949年1月25日,上午,母亲见父亲的呼吸渐趋微弱,她和外婆赶紧带领我们六个孩子,围着父亲的床沿,我们一边哭泣,一边断断续续地唱着:“到时行完一世路程,靠托主恩完全得胜,死亡冷河,我不怕过,因有耶稣亲手领我!”最小的弟弟只有两岁,还抱在母亲怀中;他不懂发生了什么事,看见哥姐们在哭,他也大哭起来。
可是,母亲不但没有哭,她还安慰我们说:“不要难过,因为有一天我们还要和爸爸在天家相聚,而且永不分离”。我泪似泉涌,跪在父亲右侧床沿,双手一直紧握着他的右手,在茫然迷惘中,我只感到无所依傍。父亲双目紧闭,仿佛已经安睡,我却感觉他的右手渐渐由软变硬。我想到,我和弟弟妹妹们已成为没有爸爸的人了。
当时,上海局势紧张,社会一片混乱,因为中共的解放军很快要打过长江来了。亲友们先后离开上海出境。寡母上奉71岁的老母,下荫子女六人,她独自一人要扛的真是千斤重担!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不懂为何会39岁守寡,和父亲结婚只有短暂的16年;16年中,二人从来没有拌过嘴;如今孩子们幼小,长子刚过14岁;前面的路在哪里?一个人带着六个孩子,怎么去走啊?
神给母亲的应许是:“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申命记》31:8)。主又用他的话安慰母亲:“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垣常在我眼前”(《以赛亚书》49:15-16)。
1951年,为了要落实父亲生前多年在南京置办的房地产产权,母亲要只身去南京与房管局交涉,首先要证明这些产业不是“敌产”,而是属于我们的私人房产。
可是谈何容易!中共的新政权虽已成立两年,母亲也多次向南京市人民政府书面请求发还这些房地产,以应付我们的生活所需。苦苦等待了漫长的两年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母亲虽会料理家务,却没有涉足世事的社会经验。要她只身面对老谋深算的“红色”政府干部,她心中的确有些担惊受怕。但天父赐给她的话语是:“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赛亚书》51:12-13)。
神赐给母亲一颗智慧和勇敢的心。在世人看来,她只是一个没有任何靠山的寡妇,一个丝毫不懂应该怎样维护个人产权的家庭主妇,而且又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寡妇。但是,万军之耶和华却是她最大的依靠。
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这样一个41岁的弱小女子,单枪匹马,竟然办妥了两年没有消息的南京房地产产权!这是因为“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诗篇》68:5)。
母亲高兴地回到上海,时值五十年代初期,虽然共产党政府每月付给母亲170元人民币作为房地产租金,但房屋年久失修,每月扣除房屋内外的维修费用后,剩下来的钱才是我家唯一的收入。除了“吃”,还要负担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的学费及衣着。
即使家中米缸就要见底,母亲也不惊慌。她心中一直有平安,相信神必有预备。就在她静心等待的时候,有人敲门,想不到是附近米店送来一石大米。母亲对送米的人说:“你们送错人家了,因为我没有去你们店里买过米啊!”那人却回答说:“我没送错!有人付了钱,就是要我把这一石大米送到你们这个地址。”
后来,母亲才知道这一石大米是一位教会的姐妹送的。奇妙的是,这位有如此爱心的姐妹又怎么知道我家下顿就没米呢?神的时候,永不误事!神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利米书》49:11)。
1952年,我就读上海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名“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是住校生。在那个周末回家,母亲立即告诉我家中“断粮”和“得米”的奇妙见证。如今时隔73载,我的两位妹妹仍清楚记得这件奇事。家中以后的年日,如神所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列王纪上》17:14),而“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记》42:3)。
1954年前后,全国推行“公私合营”政策,政府用堂而皇之的名义化私为“共”,私人房地产一律归人民政府。每个月,母亲收到的只有一百元左右的所谓“定息”。可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原来中共自己规定的“赎买政策”的“定息”也没有了,因为“定息”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统统取消。好在我们子女六人还都有工作,虽然都是“低收入”,但靠着天父的恩典和带领,我们一步又一步都走过来了。
母亲的中文及英文均有很好的根底,她是我们子女六人学习英文的启蒙老师,后来惠及我们六家人的后代,他们都上过“奶奶”或“外婆”所教的英文课。
父亲归天未久,他的一位生前好友王造时曾规劝母亲到他创办的私立学校“上海前进中学”教英语,既可走进社会,所得工薪也能养家糊口。可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一直保守母亲只做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在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浩劫中,除了被抄家,母亲未受到其它冲击。如若当年她去中学教英语,按她家庭出身,自幼接受教会学校教育,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还有海外关系,我不敢想象我的母亲在“文革”中该有何等可怕悲惨的遭遇!
在上海虹口灵粮堂,母亲是多年的教会执事。她和另一位执事(邬妈妈)常常热心探访教友。每逢礼拜一,总有近十位肢体参加在我们家的祷告会,以主内姐妹为多。尽管经济收入菲薄,母亲一定会准备午餐,接待来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午餐十分简单,只是青菜煮面条,但大家吃得很开心,彼此还能有灵里的交通。
母亲每天的灵命生活,常常从早晨开始,她每天的一半时间都单独跪在神面前祷告,数十年来,从未间断。她十分重视奉献,常常超过十分之一。手头虽然难有多余的人民币,她也一定做到除了主日为上帝奉献以外,还按月接济一位比母亲年老的孤寡姐妹。正如保罗所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后书)6:10)。
母亲一生顺服我们在天上的父。自从先父离世,她克服世上种种艰难苦困,养育我们弟兄姊妹六人成人成家。我们看到的母亲从不忧虑烦躁,总是满有喜乐平安,我从未看见母亲哭过,但妹妹告诉我,1955年10月上海第一医学院分配我到河南工作,当我第一次远离家门乘火车去郑州的那天早上,母亲上楼哭了一场。
此后的数十年中,我和母亲聚少离多,只有每年寒暑假时,我才可以回上海与家人相聚,但“反右”和“文革”使我多年有家回不得,因为我是被审查的“阶级敌人”。(下图:我母亲的见证,第一页)。
小阿姨全家于1951年离开上海,后来定居洛杉矶。1980年,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美国。1981年,小阿姨邀请先母来美探亲,我大妹妹的两个女儿也要来美念书,小阿姨的女儿(我的表妹)提供“经济担保”。母亲一行三人顺利办好护照及签证后,在1981年6月到达洛杉矶。受小阿姨、小姨夫和表妹们的盛情接待,母亲在小阿姨家快乐地住了半年,和小阿姨全家畅叙别情后,就来北卡州(NC)温斯顿-塞勒姆(Winston-Salem)和我住在一起。(下图:我母亲的见证,第2页)。
因为我们的神“行奇事不可胜数”(《约伯记》9:10),我们母子自从1980年在上海一别,一年之后竟会在美国团圆。虽然佑安母子仍在上海,时年70岁的母亲来到我身边,是天父赐我的大福。她每天照料我的生活起居,解我孤单,为我及亲人们祷告。我们母子在周末参加华人查经,主日参加美南浸信会敬拜。母亲曾应邀在主日聚会向美国的弟兄姊妹讲述父亲归天前后,她在神的面前如何学习信靠顺服。她也多次到华人教会、老人院等处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左图:我母亲亲笔写下的英文见证)
在温斯顿-塞勒姆的几年(1981-1985)中,尤其在圣诞节及其它节日时,我和母亲常参加美国朋友或鲍曼·格雷医学院举办的一些社交活动。母亲还为美国朋友们演示馄饨、炒面和春卷等“上海味”烹调。
母亲努力遵行圣经教导,正如保罗所说的那样,她“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后书》6:10)。
1989年是先父归天的四十周年。感恩聚会时,母亲对我们说,这过去的四十年,是信实可靠、又真又活的神带领她和这个家走过的四十年。神拿走了母亲的依靠(父亲、房地产、亲友们等等),使她只依靠天上的父神,过一种完全交托,信靠顺服的地上生活。四十年来,长子被划成“右派分子”,送交劳动教养;“文革”中又成为“牛鬼蛇神”,多年不得回家;其余五个子女均因家庭出身,无论升学或工作也都多不顺利;又经历“文革”风暴,家中被“抄”多次;住房楼下两间房还被查封。在那些乌云密布的日子,天上的神说:“你不要害怕!……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以赛亚书》43:1-3)。神的话和母亲每天敬虔的祷告,就是她在试炼中得力的源泉。她最喜欢的赞美诗是“数算主恩”,是我和弟弟妹妹们从小就会唱的,也是我们家中庆典(生日和圣诞)时必唱的诗歌之一。
母亲秉性安静,遇事不急不慌,一生顺从天父。再大的事也不能震动她心灵深处的平静、安稳及喜乐。她不为明天忧虑,凡事交托,也从来不服用安眠药。在我经历“反右”及“文革”的多年中,母亲一直写信安慰我,鼓励我要有信心。在人生的苦难中,她常弹奏圣诗,赞美天上的主。(上图:我的母亲)
我们家里共有三位弟兄姊妹先后定居美国并在北卡安家,母亲在各家轮流居住,是我们每家三代人共同的属灵领袖和“守望者”。
1988年10月3日,母亲从我妹妹家写信祝贺我54岁生日,引用《诗篇》59:16-17的话:“……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作过我的高台,在我急难的日子作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与我的神。”她用祷告托住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美国,我和母亲一起生活了22年(1981-2003)之久。天父补偿了我和母亲在国内不能聚首的年日。
母亲在上海时就患有多年的高血压病,还有胆结石。她1981年来美国,虽然没有任何医保,我们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始终保守她身心灵平安健康。1993年,她取得“绿卡”;1998年,87岁时成为美国公民,自此,每月收到政府发放的社会安全金(Social Security Income)500美元左右。除去奉献等等,我为她将为数很少的余额,放在“投资”计划中。
2003年12月15日,时年93岁高龄的母亲行完人生旅程,平安离世,回归天家。在她最后的日子,我的大弟弟两次专程从安庆市赶来护理她。
慈母离世时,我们想不到她的“投资”账户竟增值积累了五位数之多,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因为我自己的投资账户在股市低迷的同一时期亏损很多。天上的父神在母亲的“小钱”上,大大赐福于她。正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拉基书》3:10)。因此,母亲的丧事殡葬等一切费用,我们作子女的没有拿出一分钱。不仅如此,母亲还有余款分别奉献给格林威尔华人基督徒团契、洛丽华人基督教会;并分赠有需要的肢体等。
我虽然只享受了14年短暂的父爱,天父却怜悯我,使我在温馨的母爱中度过了60年!母亲那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始终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回忆,是有一次我们到妹妹家看望她,临走时她对我说:“我心里难过,大儿子要走了。”她拄着拐杖,从里屋走出来,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全家远去。我只是把车窗打开,向她挥手而别。“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情此景,令我终生不忘。
今天,没有人能告诉我这91岁老人的人生道路还有多长,但我深信天父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以赛亚书》54:10),因为他对我的爱是永远的(《耶利米书》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