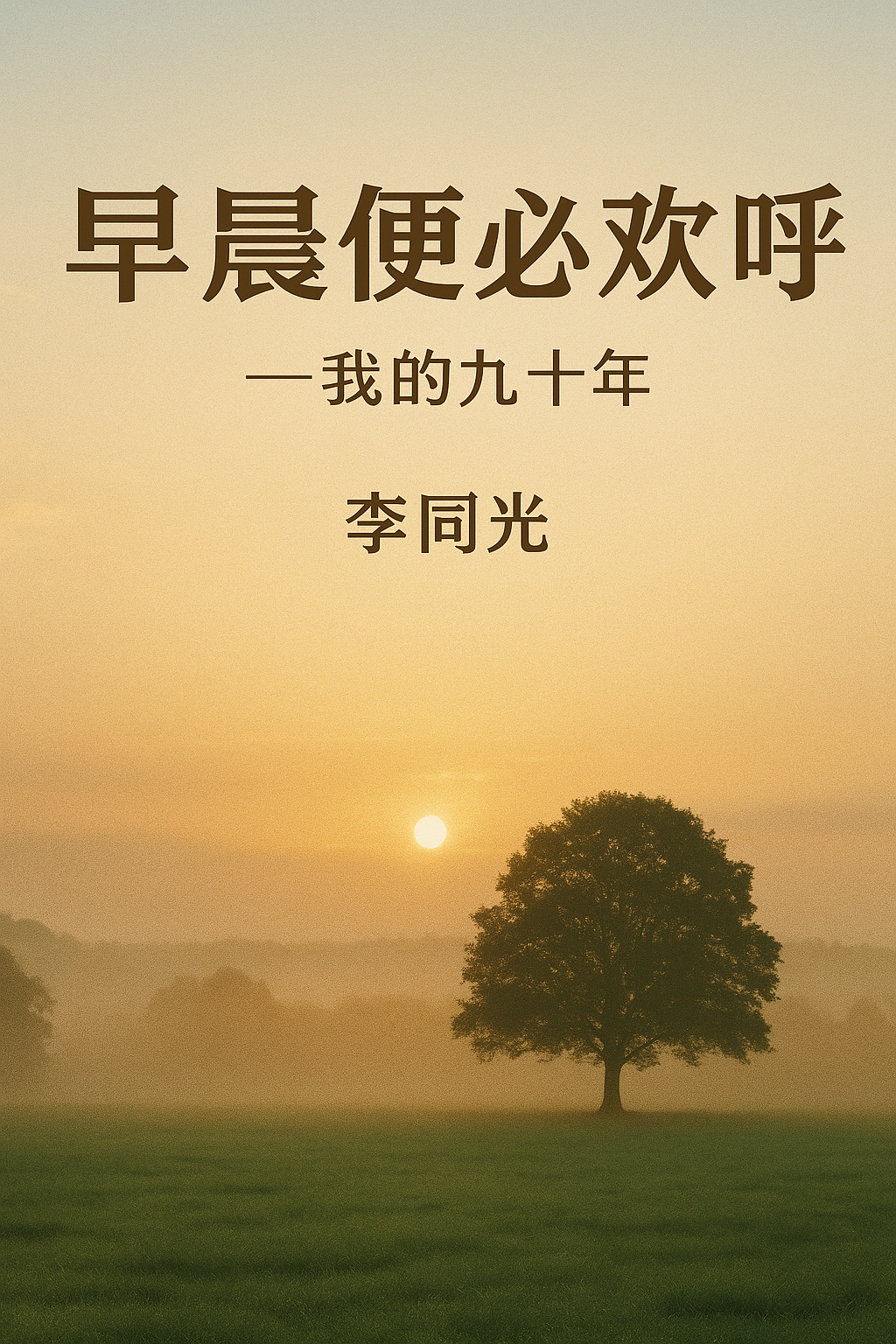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一章
第一部:骨肉至亲
第一章
我的父亲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诗篇》116:15)
先父李捷才(1900-1949),在世时很少有机会和我说起他的成长经历,因为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十四年。
父亲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的钱山。1947年,我们在南京时,我的堂兄曾对我说过,先父幼年痛失双亲。1916年,他16岁,随年长的叔伯兄弟们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回国从政,先后在南京市政府、湖北省政府,以及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多年,直到1948年秋病休为止。
先父一生仕途的最高职位,是他28岁(1928年)任首都南京市政府社会局长。
1932年,父亲和母亲在上海结婚,父亲32岁,母亲22岁。婚后,母亲、外婆等亲人不懈地为他恳切祷告,婚后十年(1942),他终于悔改归主。
此后,他不但戒了香烟,而且在重庆南岸黄埆垭救主堂的筹建工作中,努力为主做工,前后奔跑,其价值远超此前他在国民政府任职时的任何工作。
我深信父亲为天父所做的圣工,必蒙我们的神悦纳。
父亲生前曾有许多政界朋友、我于1948年在南京念金大附中时,父亲告诉我,王造时和彭文应二位先生是他从小在一起的江西安福同乡,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
父亲16岁时东渡日本,王造时和彭文应后来从清华到美国。1945年,我在重庆南岸黄埆垭家中,首次见到王造时,那时他在江西创办《前线日报》。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父亲和我与这两位好友曾在南京和上海多次见面。
父亲去世时,王造时和彭文应都是治丧委员会成员。未久,他们两位都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二人积极拥护中共党。“抗美援朝”时,彭文应是代表上海人民去朝鲜慰问“志愿军”的代表团副团长。
1957年,彭、王二人沦为全国知名大右派。王的右派帽子于1960年9月29日摘掉,正逢我被拷进“拘留所”的那个难忘的日子。1966年文革开始,王造时被揪斗,并于1966年11月被捕;1971年8月5日在上海屈死狱中[1]。彭文应是全国90名“不准平反”的右派之一。待我最后于1978年第二次平反,王造时和彭文应早已先后辞世。
父亲生前的两位挚友均家破人亡,万分凄惨!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虽然短暂,但我童年时他给我的教诲,字字句句刻骨铭心,使我终生不忘。我上小学时(1942-1946),父亲在家里教我读唐诗、《古文观止》及《曾文正公家书》。抗战胜利后(1945-1948),我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念初中;平时住校,只在周末回家。父亲请专人每周辅导我的中文及英文,并谆谆告诫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满口英语却不通中文。他还多次对我说:“你现在刚进初中,中文还差;等你高中毕业,有了中文底子,我一定把你送到美国去念大学”。
父亲要我爱惜时间,不要把时间“化整为零”般地浪费掉。他还要我长大成人后,要有“经济头脑”,学习如何向银行贷款,再去投资房地产等等我当时听不太懂的事。
父亲告诉我,日本人从小注意锻炼身体,喜欢运动。他在日本时,学会了骑马,还曾在北海道破冰游泳。他希望我有朝气蓬勃的性格,要我多运动,而我始终不擅长运动,更不知怎样才能活出“朝气”来。
追忆1937-1945年抗日战争年间,我们在有“天府之国”美名的四川,经历过生活物质匮乏的日子。我家在重庆南岸的日子,父母用各种方式接待来自沦陷区的神的仆人们。他们的家人有的还在敌后。父母帮助神的仆人们在生活和经济上的需要,我们从小就耳濡目染,记在心里。我和弟弟妹妹们长大成人后,也效法父母,用行动关爱神的仆人们,但远远没有当年父母做得那样好。
1948年12月,父亲胃癌晚期,大姨夫妇邀请我们全家从南京迁到上海。大姨家四口人,住房并不宽敞,但他们用基督的爱,诚挚地接待我们。当时,我是一个混沌未开,刚过十四岁的少年,只晓得兵连祸结,人心惶惶,因为解放军准备打过长江,国民政府已迁往广州,市场一片混乱,能离开上海的人都四海为家了。那时父亲病情加重,已有腹水,进食很少。我却一点都不懂应该如何去接受父亲即将离世的严酷现实。
1949年1月25日上午,父亲在上海家中被主平安接走。这新家的住房是母亲在四天前刚刚买下的。
父亲的追思礼拜及葬礼由杨绍唐牧师及贾玉铭老牧师分别主领;我泪眼模糊,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更全然不懂的是,父亲离世,但共产党来了,出身反动家庭的沉重帽子,就必然要套在我的头上。
一周后,我在上海横浜桥东宝兴路怀恩中学插班,念初三。怀恩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圣经是必修课,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学校教室上圣经课。
授课老师朱照爱,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语系。那天她讲的是拉撒路死后四天复活的神迹奇事(《约翰福音》11:11-44)。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朱老师反复念这段经文,使我突然觉得主耶稣在2000年前对马大说的话,好像是专对我说的。
我和朱老师过去并不认识,但天父借朱老师的口,用主耶稣说过的话,深深安慰了我这刚刚失去父亲的懵懂少年。回想起来,这一切仍像昨天发生的事。
2020年,当年在怀恩中学与我同班的锦文姊妹告诉我,朱老师已近百岁,在新西兰定居。
位于上海市闸北区闸北公园附近的浸信会公墓,大约建于1900年。1933年,大我一岁的姐姐因麻疹并发肺炎去世,即葬于此。大理石墓碑上,有父亲的手迹(姐姐的出生及离世日子),还有姐姐的一幅照片。想不到十六年后,父亲回归天家,也葬在这处公墓里。
1967年12月,外婆89岁离世归天。正值“文革”期间,虽然我在被“审查”中,但豫北医专领导仍特准我回上海奔丧。那时全国上下一片混乱。红卫兵及造反派山头林立,各自为政。无论政府机关、学校或工厂,几乎均处于“无政府”状态。
丧假很短,我仍去凭吊18年前埋葬父亲的浸信会公墓。绝未想到的是,公墓面目全非,墓园只剩下一个个的空穴。埋在地底下的棺材和其中的遗骸,不知所终;举目望去,一片荒凉。悲戚之情,不堪名状!
旁边有人告诉我,不久前,好几群红卫兵来到这公墓大破“四旧”。他们不但彻底砸碎了所有的大理石墓碑,还挖空了所有的坟墓。
还有人告诉我,棺材大多选用优质木材制成,疯狂的红卫兵们不仅掘空了墓园中数以百计的坟墓,还把棺材拉到家具厂去做家具。
多年后听说,文革结束,上海市人民政府就在这浸信会公墓原址,建了一家机械工厂。
我的父亲、姐姐,和一百年来先后埋葬在这墓园里的许多基督徒,因为毛泽东等人策划的“文革”,虽然失去了在地上的葬身之地,但我确信,在永恒的天家,他们“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哥林多后书》5:1)。
[1] 参考资料:《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作者: 叶永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01年。王造时(1903年9月2日—1971年8月5日),生于江西省安福。1925年从北京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赴美;1929年6月获威斯康辛(Wisconsin)政治学博士学位。1936年,他在上海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等六位爱国人士因反对国民党不抗日而被捕,此为震撼全国的“七君子事件”。1957年,王造时在上海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期间,被划为“大右派”,闻名全国。1960年9月30日,被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开始,他被揪斗,并于1966年11月2日被捕,被捕羁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1971年8月5日,因肝肾综合症病逝狱中,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