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知明自序:《楚国八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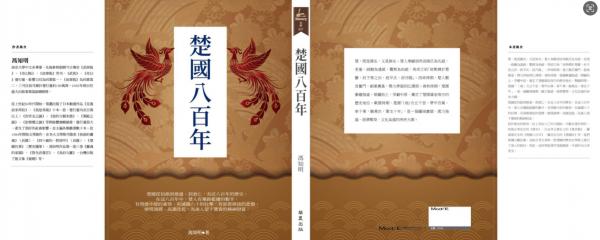
1.听说有个古老的国度——楚国,还有一个周天子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期间,成长于一个贫瘠的乡村,又恰逢轰轰烈烈的红色运动,而“文革”最大的特点是排斥知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基本是无书可读,更不了解中国有几千年文明史。
初识历史,缘于一次争吵。我记得幼时去我们的一个小镇上,走到一家裁缝店的门口时,看到店里的裁缝左手拿着一把尺子,右手握着一把沉重的裁缝剪。这个人的形象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是个细高个儿,尽管不能说他满脸横肉却看起来很暴戾,他也确实是我们小镇上出了名的混混儿。我们都叫他狠人。他的右眼上吊,估计是眼睛上长过什么疮疤留下的纪念,因为他眼睛斜斜上吊,使他的眼睛看起来白多黑少,平常他不斗狠时,也给人一副恶狠狠的印象。那天他和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斗起狠来,冲着那人大吼一声说:“你想不服周?”且双击手中的剪刀和尺子。
“不服周”这三个字那天我是第一次听到,可却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估计这是一句非常厉害的话。我便去打听了好几个上年纪的人,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是一个叫楚的国家,楚国人是被周朝的天子管着的,“不服周”就是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的意思。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个古老的国度——楚国,还有一个周天子。
因幼时家境贫寒,母亲常把我们弟妹送到外婆家去。外婆家的光景也好不到哪里,只是她是我们这里方圆几十里一个有名的巫婆。外婆家住在一个叫马港的河堤上,这条河是汉水的一个支流,这个支流通过汉水流入长江。外婆家的那个村子后面,种着连成一片的桃林,每到三月间便会开满嫣红的桃花。外婆的家乡,给我的幼年童话一般的感觉。
那个时候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穷人家生病后都会企求于巫医,或者说这也是楚地的一个传统。所以找我外婆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我还记得在农闲的时候,她家的那个河堤下,经常泊满了几十条大小渔船。那些治好病的人都会来给菩萨们烧香还愿,鞭炮整天响,他们还会送许多比如桔子罐头饼干糕点之类的廉价礼品给外婆。那可是我们当时向往的美食。
外婆有时会在盛大的巫节里跳大绳,她会唱一些谁也不懂的古老的歌。我清楚地记得,她的尾音用“兮”来结束。当时我的舅舅告诉我说,迷信的人必须会“懂古话唱古歌”才行。外婆曾亲口提起过“屈大夫”。她没有说屈原,也没有说屈子,而说屈大夫,这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以为屈大夫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赤脚医生之类的人物,我特意问过她,结果她说这是几千年前的一个古人,这应该算是我第二次与楚文化接触。
2.外婆以及她的巫术,是与楚文化密不可分的

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史上称之为改革开放的年代的。我高考落选后回到农村,到了一个乡镇企业做工人。有一段时间对唐诗宋词有了兴趣,但那时最感兴趣的就是屈原,花了一月有余的时间,把屈原的《离骚》背了下来,并逐字逐句去理解。就是到现在,近二十年过去,我醉酒时也会炫耀一下我的楚文化知识。当众背诵这些谁也没有兴趣,谁也不会听懂的楚辞,实在让人喷饭,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楚文化成了我的某种情结。
大约就在六七年以前吧,我以外婆为人物原型构思了一个长篇——《四十岁的一对指甲》,我当时单纯地认为外婆以及她的巫术,是与楚文化密不可分的,如果是要写外婆,必须得对巫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于是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买了几十本楚国历史、文化、考古等方面的书籍,边研读边随手写一些关于楚国历史文化的读书笔记,支离破碎地存放于电脑中。《四十岁的一对指甲》完成之后,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有出版,也就使我对楚文化的热爱有所减退。
今年上半年,有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武汉市的汉阳镇回乡下,当时车上有一个人说到汉阳有个桃花夫人庙的事,我便随口谈了谈息妫夫人的故事。晚上返回时,我查了一下桃花夫人的资料,随手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一个美女引发了两场灭国之战》,放到我的新浪博客上。哪知道这篇文章被引荐到了新浪的首页,仅一个晚上的访问量就高达二三十万。因为点击率这么高,重新激发了我对楚史的热情,就是说热爱楚文化的人比我想象得要多。我有兴趣整理过去的一些读书笔记,或查看一些资料,以一个《楚国往事》的书名,慢慢地成就篇章。
我在新浪博客上写楚国往事,有一个令我感到汗颜的做法,就是为使它有点击率,或多多与读者交流,把我的文章标题都取得耸人听闻,有些内容也写得颇有噱头。但是现在静静地想来,不能这样耍历史的花招。尽管我见识颇为浅显,但我感到这是在写历史真相时,就不应该过于哗众取宠,也就端正态度,认真起来,但写出的文字,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楚国文明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文明之一,因为我们的史学传统是以中原文明的正统历史为主导,对楚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楚文化给人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亦很是痛心。
3.为楚文化的辉煌而感动,为它的衰败而痛心

从我的家谱了解到我的先祖是从江西带来的,我也许是正宗的楚国的后裔。其实,你只要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你必会“楚”化,当面对这样的王朝和历史,不可能没有话说。所以,我写楚国往事,也有一种使命感。其实,我的职业是一个编辑,我的业余爱好只是写写小说,我是一个历史知识十分欠缺之人,在写这些楚国往事时,因为自己所获得历史知识有限,很多地方写得很是拮据。所以这本《楚国记事》,只能算是我自己的一点心得和读书笔记。
楚国的历史过于久远,史学家对一些楚史争论不休,比如楚国的迁徙史,比如楚国最初的都城丹阳在何处?我只好按照自己的理解,而取其中一说为是。有些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因为史学家的记录与我摘取的角度不同,我寻找这方面的资料过于吃力,只好采取演义的手法对他们进行小说化处理。比如说楚国的早期领导者熊绎、熊渠,关于他们的资料很少,可他们却是楚国发展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我不可能不涉猎,对他们只好采取演义式的做法。再比如楚庄王继位后三年,曾被叛乱者挟持出城,有两种说法相互矛盾,使我难以认定,只好含糊其词。
我为楚文化的辉煌而感动,为它的衰败而痛心,使我的立场失去了公正性。站在它的立场上,对楚国的霸道行为视若无睹,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对许多被灭的小国是有欠公允的,比如蔡国、徐国。所以《楚国往事》还带有过多的偏见。为此,我对一些遭受楚国欺凌而又顽强生存的小国,很是抱歉。
纵观这本《楚国往事》,谬误之处颇多,无法一一列举,好在关注楚文化的专家学者很多,我希望通过它的问世,权当抛砖引玉之用,亦能够校正我的谬误,以免误人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