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梦泽》的深度对话:文学的纯粹与通俗之辩

2023年4月,两位资深作家——一毛与黑哥,就一毛的近作《云梦泽》(海外书名《生命中的他乡》)展开了一场长达5000余字的文学对谈。这场对话不仅是一次私人交流,更是一场关乎文学本质、创作理念与时代背景的深度思想碰撞。黑哥以其一贯的“纯文学”视角审视作品,既给予了高度肯定,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毛则坦诚回应,剖析自己的创作初衷与困惑。以下,我们将这场对话梳理成文,并分为几个核心议题进行探讨。
一、作品的体裁之辩:通俗与纯粹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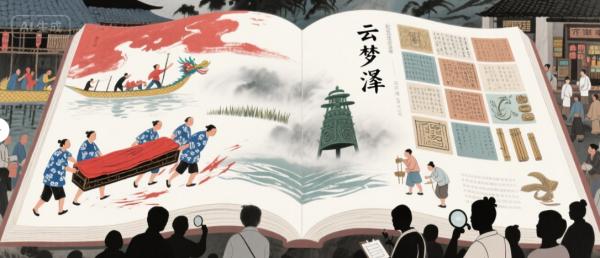
对话伊始,黑哥便将《云梦泽》定义为“通俗文学”,这成为整个讨论的基石。他坦言自己很少阅读通俗文学,因此难以精准评价,但这一定位并非贬低,而是基于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
黑哥的观点:
成功的通俗性:黑哥首先肯定了《云梦泽》作为通俗文学的成功。他认为小说“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楚地的所有特点,从社会学、民俗学、地域文学、历史学等多个维度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故事组织和叙述“非常好”,特别是对抢尸等场景的描绘“写得很精彩,传神”,这些都保证了作品的吸引力与广阔的读者基础。
纯文学的评判标准:黑哥心中的“纯文学”标准是:以美、情、哲理为核心,能够感动人、引发深思,并具有美学价值。他强调,好的纯文学作品是百读不厌的,如他反复阅读的沈从文的《边城》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他认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以人物情感和内心世界为主,故事只是背景;而后者则常常是“故事掩没人物”。
一毛的回应:
职业影响与自我坚守:一毛坦承自己长期浸淫于通俗文学领域,从《今古传奇》到武侠小说,再到网络文学,他身处其中,但始终保持着一种“病态的”排斥。他刻意在《云梦泽》中“消解了故事”,甚至自认为“提高了这个高度来认识”通俗文学的污染性。因此,他认为《云梦泽》并非国内语境下的通俗文学,出版社也因其非通俗的写法而不看好其发行量。
与世界文学的对照:一毛也承认,如果将黑哥所列举的《飘》《基督山伯爵》等世界名作归为通俗文学,那么《云梦泽》被这样归类他“当然无话可说了”。这显示出他对文学分类的开放性,以及对黑哥评判标准的尊重。
对话精粹:
黑哥:“我心中的纯文学的标准是:以美和情加上哲理,能给人以深思,感动人,感染人,又有美学价值,包括语言也有美学价值……我读你的长篇……有一种只见故事不见人心的感觉。”
一毛:“我是提高到这个高度来认识的。我接触了太多的通俗文学文本,太了解了它们了。所以,从国内文学层面,《云梦泽》不是通俗文学的文本。”
二、人物塑造的得失:故事与情感的失衡

黑哥对《云梦泽》最大的不满,在于“故事太多,人物情感,复杂的情感……都表示得不够”。他认为,这是区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键标志。
黑哥的批评:
人物的单薄:黑哥以重要人物三娘为例,认为她的开篇精彩,但后来却“苍白”了。尽管经历了教师父亲之死、洋庙被骗、性虐待等悲惨遭遇,但这些丰富的“故事”却“掩盖了人物”,导致她的个性和情感“单调不丰富不丰满”。
线索人物的“道具化”:对于作为叙事线索的李如寄,黑哥认为他沦为了一个“道具”,缺乏向内的性格刻画和哲学思考。这使得小说本可以借助这个人物进行人生哲理的探讨,却最终“没有用上”。
故事的堆砌:黑哥认为一毛在写作中,过于刻意地展示他对楚地风情、历史和人情特点的熟悉,“几乎到达买卖的地步”,导致“只见故事不见人心”,甚至有“为故事而故事,为新奇而新奇”的倾向。
一毛的自省:
笔力不济与时代困惑:一毛坦承对三娘的塑造“苍白”是“本人笔力不济造成的”,但他也指出,部分原因在于他对历史和一些运动的困惑,他无法完全控制笔下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走向。
人物设计的局限:一毛承认李如寄最初的设计就是“线索人物”,完成形象后也感到“缺少许多要素”,他无法找到除“笔力不济外”的更好解释。
对“故事”的不同理解: 一毛并不认为自己是被故事牵引和淹没,他强调写作初衷是“消解故事”。他笔下的故事,如冯老爹的“功夫”,是为了“折射云梦泽遗留下来的一些神奇的东西”,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载体而存在的。
对话精粹:
黑哥:“好的小说,故事可以丰富,丰满,但也不必多,尤其过多,成了堆砌。故事不必满,但故事中的人物却得丰富,丰满,甚至复杂才对。而且要有充沛的动人的情感。”
一毛:“这些是不是高度和深度不够,我认为是不够的,同意的。但是不是被故事所牵引和淹没,我并不这样认为。”
三、叙事结构的考量:单线与珍珠的取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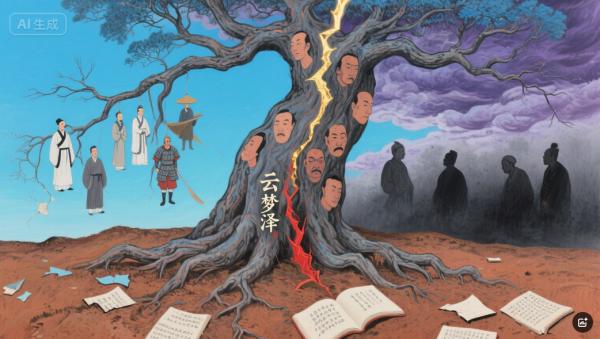
在结构问题上,黑哥指出《云梦泽》采用的是“单线条的,直线条的”结构,而他个人更偏爱“把一把珍珠散开去,但最后一定会把他们都收拢来”的叙事方式。
黑哥的分析:
优点与局限:黑哥理解一毛以李如寄为线索串联起祖上故事的构思,认为这是“有办法的办法”,但这种“像一棵大树”的结构,使得整个长篇的人物难以“有机地整合一起”。
缺乏内在联系:黑哥认为,由于这种单线条的结构,导致了人物的缺失和叙事的断裂,比如李家兄妹在后半部很难再出现,这使得作品的整体性受到影响。
一毛的阐述:
对“三部曲”的排斥: 一毛坦言,小说构思之初曾考虑写成三部曲,但他最终放弃了,原因有三:一是害怕落入成名大家的套路,失去自己的个性;二是担心如果用通俗文学的写法,会让故事过于离奇和肤浅;三是为了“消解故事”,避免写作初衷的偏离。
结构探索的代价:一毛承认这种结构“是有缺陷的”,但他认为这是自己“迄今为止找到最好的表现方法”,并且这种探索性是他写作态度的体现。他甚至为此牺牲了李如寄这个人物,也刻意让某些人物“彻底地消失”,以制造悬念,应对单线条的弊端。
对话精粹:
黑哥:“我常常喜欢把一把珍珠散开去。但最后一定会把他们都收拢来。我常常是这样的。散开去,再收回来。”
一毛:“这个结构是有缺陷的,但是我迄今为止找到最好的表现方法,毕竟花了十几年,有点浪费。”
四、文学的价值取向:美学与社会学的衡量

黑哥在对谈的最后,再次强调了他对文学的评判标准。他认为,虽然《云梦泽》在社会学、民俗学和地域文化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其文学和美学价值相对不足。
黑哥的观点:
写实手法的肯定:黑哥高度赞扬了一毛的写实手法,认为他“状物述事,对话等,都有红楼笔法了”。他承认这是《云梦泽》超越一般通俗文学的地方,也值得他学习。
美学价值的缺失:尽管如此,黑哥仍然坚持“小说是写人物的”这一核心准则。他认为,一部好的小说,应该能给读者留下“一个永远记得住的人物形象”,就像《飘》中的郝思嘉或《红楼梦》中的经典人物。他甚至坦言,对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持有相似的看法,认为它虽然伟大,但没有留下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
一毛的认同:
文学首重写人:一毛完全同意黑哥的观点,即“文学美学就是写人看人的”,他认为民俗、社会学、历史文化等都是“附庸于上”的。他承认自己的写人“不充分”,这是作品的缺憾。
对《百年孤独》的共识:一毛表示,他对黑哥关于《百年孤独》的看法“一样是认同的”,这再次显示出两位作家在文学根源和品味上的高度一致性。
对话精粹:
黑哥:“我觉得你这部作品在文学,美学上的价值是不如社会学,风俗民俗学,地域文化,对故乡的回忆和感情上的价值的高。但我的要求是文学上,美学上的。”
一毛:“我同意黑哥的看法,文学美学就是写人看人的,一部作品首先衡量的写人是否成功,再看其他。”
五、总结与展望:在坚持与探索中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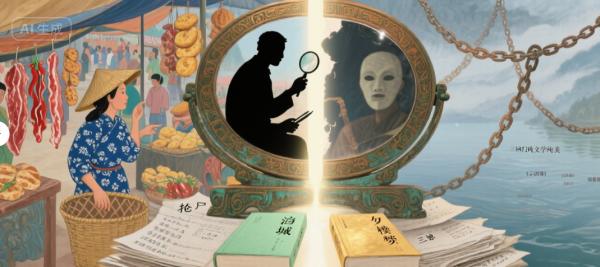
这场对话是两位作家真诚而深入的文学探讨。
黑哥以其“纯文学”的苛刻标准,为《云梦泽》提供了宝贵的、有深度的批评意见。他既肯定了作品在写实、风俗描写和故事丰富性上的成功,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物塑造的不足和结构上的缺憾。他建议一毛多读多听《边城》和《红楼梦》,以期下一部作品能摆脱故事的牵绊,回归“纯文学的纯美”。
一毛则以谦逊和坦诚的态度回应。他毫不回避自己的“笔力不济”,也承认人物和结构的不足。但他同时也捍卫了自己的创作选择,强调了作品在结构和叙事上的探索性,以及对通俗文学套路的排斥。他表示,自己的写作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下一部长篇将会有新的尝试。
这场对话的意义远超对一部作品的评判,它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理念:一种是对文学纯粹性的不懈追求,以人物和情感为核心,将故事作为背景;另一种是在商业化浪潮中对文学探索的坚守,既吸收通俗文学的元素,又努力通过结构和叙事上的创新来超越其局限。这两种态度并非对立,而是殊途同归——都指向了对文学更高维度的追求。
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 维也纳石头巷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