忒(特)修斯国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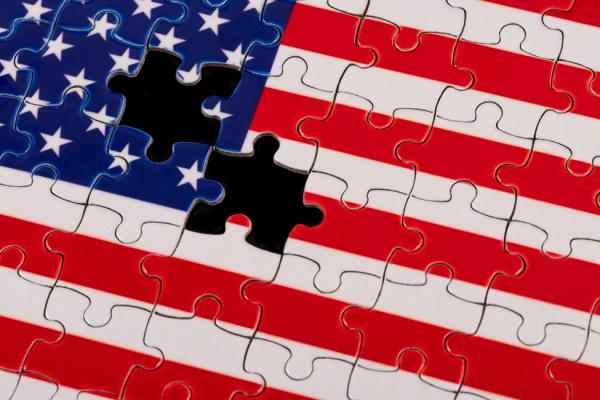
如果没有完善的移民和同化体系,美国将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国家。
克莱蒙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任川普总统时期的内政部副助理部长的杰里米·卡尔 (Jeremy Carl) 周三 (8 月 20 日) 在《美国思想》就新移民的归化问题发表评论:
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镇上的一家中餐馆墙上贴满了海军陆战队员的照片,而且总是给任何进店的海军陆战队员打折。这家餐馆背后的故事引人入胜。
这家餐馆的创始人是一位移民,二战末期,他在中国还是一个贫困儿童,后来与一队海军陆战队员结为好友。他们实际上“收养”了他,给了他营房里自己的铺位和海军陆战队制服,教他英语和基本操练,并把他送到了中国一所基督教宗教学校,费用由他们承担。共产党占领后,海军陆战队撤离了中国。海军陆战队员们称他为“双鞋查理”(“双鞋”是他们最接近他姓氏徐 (Tsui) 的称呼),他因与美国人的友谊而遭到共产党政府的迫害。政府将他监禁多年,获释后又判处他软禁。
历经重重考验,查理奇迹般地与他的海军陆战队老战友们取得了联系。1983年,中国对外开放之际,查理被安排移民美国。他定居于北卡罗来纳州,开了一家中餐馆,并最终成为美国公民。他的子女们在美国发展得相当不错。有的经营着餐馆,有的则成为了医生和药剂师。2013年,查理成为第18任美国荣誉海军陆战队员。同年,他陪同几位海军陆战队老战友重返中国,这是他离开中国30年后的首次回国。
我的目的并非重述查理的人生故事(他的故事已经是一本书的主题),而是将其作为爱国同化融入美国社会的一个极端例证。即使在异国他乡,他也始终忠于美国及其传统。即使在遭受共产党的多年迫害之后,他也从未忘记这份忠诚。查理后来搬到了美国的一个小镇(而不是某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成为了美国公民,皈依了美国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并且从未忘记带他来到这里的人。
我在阅读安德鲁·贝克的文章《同化及其不满》时,立刻想到了查理的故事。查理对美国的热爱与那些为哈努曼建造巨型雕像的印度移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贝克对此感到十分不安。这与其说是要告诉我们华裔移民与印度裔移民的区别,不如说是描述了美国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时期。
查理的例子推翻了这样一种观点:有些移民群体无法或不愿融入美国社会,而有些移民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容易融入美国社会(我们应该在接纳任何移民的前提下,优先考虑这些群体的移民)。建造巨型哈努曼雕像的人无法或不愿融入当地社会,这表明当代环境与40年前有所不同,这使得融入更加困难。
查理抵达北卡罗来纳州时,该州亚裔美国人的比例仅为0.4%左右,而这一比例几乎是十年前的四倍。这是一个新兴的群体,仍在摸索前进。著名喜剧演员肯·郑当时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度过了典型的美国童年,他在采访中深情地回忆起这段经历。
我小时候住在街上的一位朋友也是这个亚裔少数群体中的一员。在一个亚裔美国人很少的小镇——没有选择是否融入主流——她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南方文化,成为了一名明星学生和明星运动员,并且总体上与社区融为一体。她至今仍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
当我看到我最亲密的美国朋友,他们的家族来自印度次大陆时,他们的故事与这些中国移民大体相似。他们在威斯康星州的小镇、俄勒冈州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或当时白人占绝大多数的西雅图郊区长大。哈米特·迪隆(Harmeet Dhillon)是一位出色的民权助理检察长,她可能是北卡罗来纳州乡村小镇里唯一的印度裔美国家庭。
这些移民沉浸在传统美国文化中,并接受了我们的文化标准、品味、习俗和价值观。当然,他们可能保留了一些父母出生地的文化,甚至宗教观念,但他们身上最“印度”的特征是他们的肤色。他们通常比我成长过程中接触过的绝大多数努力进取、热爱学术的美国白人更保守、更爱国。因此,问题不在于某些群体能否融入,而在于我们是否正在创造一个鼓励他们融入的环境。
同化国家
正如贝克所说,同化的历史与美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我还记得小时候的一次晚宴上,我的父母(他们在俄亥俄州和亚利桑那州长大,但现在已在北卡罗来纳州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对一位朋友说,在这个州生活了很长时间才完全被当地人接受。我回应道:“是啊,你可能得在这里住十年。” 房间里的成年人们哄堂大笑,因为他们知道内战在当地仍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话题。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村长大,从小就被灌输亚伯拉罕·林肯是“魔鬼”(他的话),尽管他在课堂上对林肯的看法要积极得多!所以,作为一个中西部的外来者,我也必须融入其中——努力融入并拥抱我周围的南方文化,尽管那并非我父母的文化。任何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会告诉你,有时候你会感到不舒服或被冷落,甚至偶尔成为别人的笑柄。但最终,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正如《路得记》所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这也完美地描述了爱国同化的最终目标。
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成为优秀的美国人。印度人可以成为优秀的美国人,中国人可以成为优秀的美国人,墨西哥人也可以成为优秀的美国人。非基督徒也可以成为优秀的美国人。一些极右翼人士可能会对这种说法感到愤怒,他们指出,根据1790年最初的《归化法案》,情况并非如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而美国几乎普遍信奉基督教。
但一个多世纪以来,情况并非如此(例如,根据1848年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墨西哥裔美国人可以成为美国公民)。平均水平的日裔美国家庭是在125年前来到美国的。他们与我们共享文化,并参与了我们的战争(全日裔美国人组成的第442团战斗队是二战中战功最卓著的部队)。近三分之二的日裔美国人与异族通婚,其中绝大多数与白人通婚。即使在像我现在居住的蒙大拿州这样种族多元化程度较低的州,1870年华裔人口也高达10%,这一比例高于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当然,白人在美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将这样的移民群体排除在美国历史之外,从历史上看是完全错误的。
这并不是说种族或民族与美国身份无关。从历史上看,我们既是一个信奉特定信条的国家,又绝大多数人来自欧洲。就我们是一个信条国家而言,我们的基督教文化——包括该文化的世俗化版本——也是该信条的一部分。
但保守派作家兼《火焰报》主持人奥伦·麦金泰尔(Auron MacIntyre)曾言之凿凿,美国性的定义“千差万别”。然而,对于那些坚持认为美国只是一个信条国家的人来说,这些信条究竟是什么?我们会驱逐那些不认同或不以认可的方式理解这些信条的人吗?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表明将美国视为纯粹的“信条国家”的想法是荒谬的。
麦金泰尔将美国比作希腊神话中的忒修斯之船。如果所有腐烂的木板最终都被替换,它还是同一艘船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答案取决于替换的原始木板的比例和速度。替换的木板与原始木板有多相似?这艘船是否保留了最初的设计?以这种方式思考美国身份认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真正的同化是什么样子。
不幸的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并没有实现那种健康的同化。新移民的数量实在太多,难以有效融入,而我们的公共文化又过于弱化,甚至无法尝试。这导致美国出现了成倍增加的52英尺高的哈努曼雕像。这应该是非法的吗?虽然最顽固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不会同意,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们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宗教观点,这赋予了他们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但是,对于融入美国规范,这究竟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法律背后的精神
华盛顿总统主张限制移民,即“通过与我们人民的融合,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将被我们的习俗措施和法律同化。总之,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民族。”詹姆斯·麦迪逊认为,我们应该“排除那些”不愿融入我们社会的人。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同样要求对所有移民进行绝对的爱国同化。虽然巨大的哈努曼雕像并不违反美国法律,但它似乎确实违背了建国先贤的精神。
正如贝克所观察到的,
多元主义本身并非目的。它源于一种基督教秩序,这种秩序自信地包容少数派观点,因为它确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权。如果这种多数派被忽视,这种自信被侵蚀,多元主义就会变成它的反面:一座充满冲突的神祇和道德的巴别塔,注定被抛弃和衰落。
他没有指出的是,不幸的是,由于美国身份的本质正受到激烈的质疑,这样的进程很可能引发大量的暴力。这甚至不是移民自身的错,但它表明了我们移民和同化战略的失败。
德克萨斯州有超过510万移民,其中包括超过45万印度移民。1940年,全美只有2000多印度人。1980年,美国的印度裔美国人(无论是本土出生的还是移民的)数量比今天仅德克萨斯州的印度裔移民数量还要少。美国人口结构失控的转变速度——即便只是在我有生之年——也令人叹为观止。即使你对印度裔美国人,甚至对印度(我曾在印度生活和旅行过许久!)怀有敌意,也能看出这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美国可以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生存下去,甚至蓬勃发展,但它应该始终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绝对多数的民族,以此来定义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像忒修斯之船,可以在多年后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同时仍然保持美国特色。但它不可能无限地改变。
在移民问题上,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法移民有限且有序的国家,要求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或者,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移民自由的国家,数百万合法和非法移民涌入我们的边境,激烈地挑战——并最终颠覆——我们对美国身份和文化的认同感。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由数量有限的“查理二鞋”(Charlie Two Shoes)组成的国家,他们完全拥护美国身份。或者,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从世界各地接收数百万既不信奉美国传统神灵,也不信奉美国传统文化的人的国家。这两条路都没有被法律禁止——但只有一种移民理念能够契合美国建国先贤所设想的风俗和传统。
(维基百科:
关于忒(特)修斯: 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神圣英雄,因杀死牛头怪而闻名。杀死牛头怪后,忒(特)修斯解救了被俘的雅典男孩, 克里特人走近并惊叹于这一幕。
关于忒(特)修斯之船: 亦称忒修斯悖论。1世纪时, 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提出:如果忒修斯的船上的腐烂的木头逐渐被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