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俄罗斯和西方千年恩怨的终极化解之路(一)
作者:高瞻
四月初,海外各家中文媒体无一例外的刊登了一篇出自外媒的新闻《普京为什么坚决不退4乌占领区 俄官员曝真实缘由》,里面说:
“总部设在荷兰、具有反俄倾向的莫斯科时报,引述一名与克宫有关官员表示,莫斯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巩固对这4个地区的控制,因为普京已经将它们的地位写入俄罗斯联邦宪法,在政治上根本无法承受放弃这些领土的代价。
这名官员表示:宪法上没有让地区脱离的机制。我们需要完整的札波罗热州和赫松州。要么川普施压乌克兰撤出,不然有人告知我们:‘启动漫长谈判,单纯使用武力建立控制’。这对俄罗斯来说是最糟,渡河作战永远很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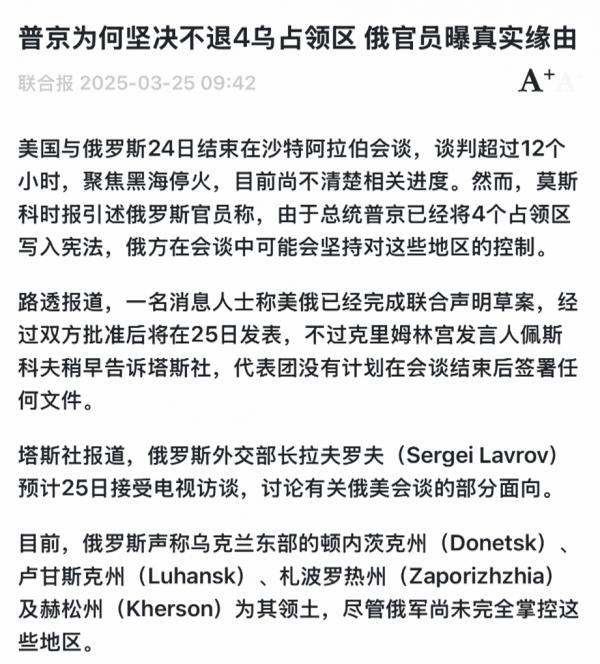
如此危言耸听的劲爆标题,竟然“曝”出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学前班程度的内容,让我不禁想到:难怪普京端坐陛上二十几年至今不落衰相,不是他本领有多大,而是欧美和俄罗斯的反普京势力水准太低了。
把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四州并入俄罗斯一事写进宪法,是普京“坚决不退4乌占领区”的果而不是因。颠倒因果、反果为因、因果不分,正是当年拜登和今天欧洲对俄乌战争束手无策、死活无解的根源。
那么,普京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韪,与整个西方和普天下人为敌,不惜国本、贴上老命,哪怕一度打得自己权力、地位和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但对“4乌占领区”就是不肯放手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2024 年 2 月 9 日上午,原福克斯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现视频平台塔克·卡尔森新闻网的创始人塔克·卡尔森在克里姆林宫对普京进行了两个小时采访。普京开始说要“花一、两分钟讲讲历史”,结果却用了冗长的时间啰里啰唆、颠三倒四的从留里克王朝开始叙述了几个世纪的俄罗斯过去,结论是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它完全是列宁-斯大林时期人为制造的错误。普京这番言论轰动了世界,让东西方反普京者一下抓住了把柄:所谓俄罗斯安全受到了威胁,所谓北约东扩和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所谓去军事化特别是去“纳粹化”,所谓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受到迫害和灭绝,全部是借口和谎言,普京根本就是要蚕食和鲸吞乌克兰、实现恢复俄罗斯旧日帝国的梦想和野心。他们故意忽略掉了普京后面说的一切:“当时俄罗斯期待着被接纳到‘文明国家’兄弟家庭中,但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欺骗了我们”、“美国政客们把我们逼到了不能跨越的边缘,因为这会毁掉俄罗斯本身”、“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仰者和本质上俄罗斯人民的一部分抛弃给这台战争机器”、“为什么在苏联解体后,对俄罗斯采取了如此错误、粗暴、完全没有根据的压力政策?……北约的扩张、对高加索地区的分裂主义者的支持、反导系统的建立……然后是把乌克兰拖入北约”,等等等;而如果无视普京后面说的这些,就不可能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根源有一个全面、完整、深刻、真实的理解与认识。

我上高中的岁月,正是1980年代北京高校竞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那时北京在校的大学生们,有的刚刚经历了民主墙运动的强烈冲击,有的正在沐浴竞选活动的峥嵘洗礼,即便是行为上远离政治的普通学生,也罕见的清醒、深刻、叛逆甚至急进。就在此时,一批来高中实习代课的北师大男女生们,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77至79级大学生以及他们的深邃和广博——其实这些男女生还属于当时在大学同级里年龄最小的应届高中毕业考生——。至今,我仍旧清晰地记得我和其中一个对欧美文学如数家珍的中文系女生的对话:
“苏联虽然和中国的制度一样,但它精神的丰富、思想的进化、社会的进步、人民的文明,中国是无法比拟的。在苏联,还曾产生了好几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这在解放后的中国难以想象”。
“那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毕竟,苏联的文化重心是在欧洲”。
要知道,那是1981年。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勃列日涅夫统治的临终期,一个斯大林之后最黑暗、最腐朽、最停滞、最窒息 、最专制,但从外面看上去也最鼎盛、最强霸、最将千秋万代的年代。勃列日涅夫沉疴已久、尚未咽气;还在“七上”年龄的安德罗波夫未老先衰、重病缠身,但命中注定还有一个短暂机会让他最后绚烂绽放;72岁的契尔年科奄奄一息、苟延残喘,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还会在临死前大捞一把;戈尔巴乔夫虽然朝气蓬勃,却只不过是政治局里一个普通成员,总书记职位望而遥不可及;苏联仍旧一如既往,雾霭沉沉、前途茫茫,未有尽头:人民看不到些许希望和光亮,人类想像不出苏联和世界将来会是别的样子。现在回头去看,我们这样的对话是多么超前和不凡。
从那以后,怎样定位俄罗斯在欧洲的位置,如何区分俄罗斯与欧洲的异同,怎样理解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如何认识这种位置、异同和关系对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国家战略以及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就成了我时常关注的课题。
在全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中,人们知道有犹太民族的“选民说”和“选民意识”、有法国人的“法兰西主义”或者更耳熟能详的“沙文主义”,尤其有美国人的“山巅之城”观念、“道德灯塔”信念、 “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精神、 “救世”思想等国家使命感和历史宿命观;甚至,连伊斯兰教徒们都敢相信自己是真主的“最优民”。但是,很少人听到过,被西方称做“欧洲垃圾”的俄罗斯人,竟然也有一种不但类似、而且成了体系的“大俄罗斯主义”—— 包括“帝国转移理论”、“俄罗斯民族救世主义”、泛斯拉夫主义、亲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等等。
大俄罗斯主义基本思想是:俄罗斯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上帝的选民,肩负着拯救人类、解放各民族的使命与职责。“帝国转移理论”是大俄罗斯主义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第一罗马”罗马帝国堕落、毁灭和“第二罗马”拜占廷帝国沦陷后,无论是罗马教廷还是“神圣罗马帝国”全都是异端和僭越,而只有俄国是上帝唯一虔诚的信奉者、基督教世界的拯救者、基督信仰的保护者、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也就是新的罗马或叫“第三罗马”。
一般人的认识里,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苦难深重、步履维艰,理应忍辱负重、砥砺前行,至少得像东欧剧变后邓小平说的那样“夹起尾巴”、“少露锋芒”、“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可其实并非如此:它骨子里的“民族救世主义”居然根深蒂固、长久不绝,成为大俄罗斯主义中另一个重要成分。而且,恰恰正是“苦难深重” 以及伴生而来“极度谦卑”、“情愿忍受苦难”的独特民族性格成了这一“民族救世主义”的来源和根据——“上帝选中我们赤贫的人民,以他们的忍耐和恭顺、平凡和卑微联合在一起,上帝选择这样的人民以真理征服世界”。“苦难意识”是俄罗斯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心理积淀,它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两种历史经历:外部是从蒙古铁骑的践踏到拿破仑的入侵再到希特勒的蹂躏,这些记忆使俄罗斯人回顾命运时与西方人截然不同,西方人自豪古希腊文明、罗马的辉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光荣革命、大宪章、大航海和新大陆、资本主义精神,而俄罗斯铭记的只有沉重、惨痛和晦暗——与此同时,他们有意无意的完全遗忘了自己给其他民族带来的苦难、沉重、惨痛和晦暗——;内部是几百年来沙皇持之以恒的残暴统治,这一统治既摧残、扭曲了俄罗斯人的人性又重塑了它的民族特性,使它在饱尝屈辱和欺侮的同时又享受着忍受苦难的快感、背负苦难的庄严和承担苦难的骄傲,甚至自信为“天将降大任”前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俄罗斯的心灵史再一次证明了,专制制度在压迫、残害一个民族时,也成功的塑造着它的变态性格,而结果是它比专制制度本身还更长久的自觉维护、顽固坚守、引以为傲这一性格的变态。这种让西方人无法理解、莫名其妙的情怀,最有代表性的是柴可夫斯基创作《如歌的行板》前被民歌《凡尼亚坐在沙发上》感动的泪水夺目时说的:“我听到了,苦难的俄罗斯人民最美丽的心声”——当然,对中国人来说,柴可夫斯基的心弦不难感同身受,因为他们同样能流畅的吟诵舒婷那首《也许》里的名句 :“也许泪水流尽,土壤更加肥沃;也许我们歌唱太阳,也被太阳歌唱着;也许肩上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
近千年里,统治和压迫者们刻意渲染、咏叹民族命运,被统治和被压迫者们从灵魂深处相信和讴歌“多难兴邦”,从当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罗斯人是拯救者——拯救人们免受蒙古压制的拯救者,他们竭尽全力阻挡蒙古人,不许蒙古人进入欧洲,他们是保护欧洲的一座墙,被敌人摧毁了一半的一座墙”,到后来苏联历史教科书里写“俄罗斯人民忍受着巨大的苦难,坚持同残忍的征服者进行斗争,保护了西欧免于蒙古恐怖的枷锁”,再到今天俄国全社会确信“蒙古之后,俄罗斯又几次拯救了世界和欧洲:十九世纪初粉碎了拿破仑的入侵和最后打败法国、一战里为战胜威廉二世发挥了决定作用、二战中再次从希特勒手中解放了欧洲”,俄罗斯民族同仇敌忾、众志成城、齐心戮力、上下一致,把自强精神、救世主义最终异化为后面要说的主动征服世界的思想和行动。
在“大俄罗斯主义”、“帝国转移理论”、 “俄罗斯民族救世主义”的精神氛围下,和大多数人想象的正相反,俄罗斯千年历史中只有极其短暂的几段时光——比如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叶利钦的一部分执政期间——倾情西方、崇尚欧洲、醉心“西风东渐”、渴望“脱亚入欧”、呼唤欧风美雨,而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从意识和灵魂深处与西方格格不入,否定走西化道路,强调与西方文明的对抗性,视欧洲化为对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威胁,认为必须保卫俄罗斯对抗拉丁—日耳曼文化的智识殖民。就像赫尔岑说的:“亲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理论或学说,而是受到伤害的民族感情……即对外国影响的一种反作用,而这种外国影响从彼得一世最初让人们剃胡须时候起就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