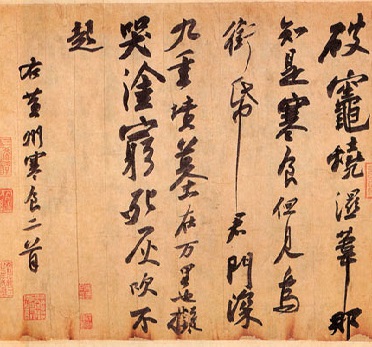告别记忆
人晚年生活的主旋律是告别。
我们告别亲人,告别朋友,告别师长,告别故乡,告别以往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甚至告别自己的母语 ……, 然而现在到来的这个告别却是特别地沉重。
它来得如此缓慢,貌似人道地不想对你的生活产生太突然的冲击,因而人们并不把它列入疾病之列。先是短期记忆的离别,然后中期记忆逐渐蜕变成为短期记忆,最后中期记忆离去,剩下了那些为数不多的被脑蛋白反复巩固过的长期记忆。
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失去效率的感觉。人会时隐时现地觉得技能学习和工作效率不如从前,这常常使人误认为是功夫不深或投入的时间不够。
然后影响到人的精神活动,主要是思考的习惯,思考的质量,和思考的乐趣。年轻时有什么新鲜想法,立即会衍生出很多更深更有趣的思考,你可以在较长时间里去追寻和享受这些思考。到了现在,你不得不用录音笔记录下时常出现在脑中的闪光,才有可能事后慢慢咀嚼。
当短期记忆的丧失发展到影响个人的日常生活时,人才会开始真正感到它的存在并引起对它的关注。最先遗忘的是钥匙放在哪里、刚刚想要说点啥、昨天吃了什么,亦或是才认识的新邻居的名字。起初只是笑一笑,觉得不过是粗心或走神。但当这“粗心”变得频繁,甚至影响到重要的生活细节,譬如外出忘了锁门,煮饭忘了关火,心中那道模糊的阴影便开始浮现——是不是,我的记忆要离我去了?
这不是一次使心灵震撼的别离,没有痛,没有泪,没有久久的凝视,没有徒劳的挽留,只有静静的,缓慢的流失。它不像丧亲那般悲恸欲绝,不像失恋那样心飞魂游。你睁着眼,看着记忆的树叶一片片飘落无踪,再也无法将它们重新拼凑回来。
人不过就是由躯壳和精神组成的一部生物机器。精神活动最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记忆。没有记忆的精神,就像失去了内存的计算机,不管CPU如何强大和灵敏,对人这部机器都毫无意义。记忆存储着我们曾经走过的路、说过的话、爱过的人、受过的伤、流过的泪,它是我们所有逻辑推理的基础,是我们全部喜怒哀乐的源泉。失去记忆,就像一座房子被悄悄拆除了梁柱,外观未变,但已摇摇欲坠。你还活着,却失去了灵魂的支撑。
曾经听母亲说起她的童年,听父亲讲过他的坷坎。我曾以为,这些故事自会被生物的接力棒传递下去。可如今,审视着我这根接力棒时,却突然发现,我并不具备那样的功能,或者说生物并不具备那样的功能,而且人不应该希冀那样的功能,除非你在记忆强大的日子努力做些什么。有时,我还会在梦中回到童年,梦见外婆和老屋、院中的丝瓜架、少年时的朋友们。梦中一切鲜明清晰,而梦醒之后,那些场景就像退潮的浪,带走了沙滩上的脚印。
告别记忆,其实也是一种全方位的剥离。它剥去我们虚荣,也剥去我们的谦卑,它剥去我们假意,也剥去我们诚心,让我们赤裸地,简单地面对人生最后的旅程。你的世界缩小了,从一个有纵深、有层次、有温度的立体空间,变成了一个现在进行时的静态画面。
人告别记忆的层次并不相同,就像世界上有穷人富人一样,取决于你从上帝的签盒中抽到一张什么样的签牌。《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临死前还记得油灯中点着两根灯草,挣扎着要儿孙挑掉一根以蓄家财,他的短期记忆可了得!是不是该羡慕呢?
然而,这场告别并非全然残酷。
当记忆开始褪色,往昔的伤痛也会随之远去。那些曾让人夜不能寐的遗憾与悔恨,会在记忆的退潮中被冲刷得轻盈。你不再固执地抓着过往,不再执着于谁对谁错,不再念念不忘某个眼神、某句重话。你学会宽容,学会忘记,也学会说声再见。
老年人的心,或许就是这样慢慢变得柔软随和起来的。他们忘了许多事,但感到了爱。他们不再记得自己的年纪和姓名,却记得世上最纯真的爱来自何处。我忘不了敬重的长辈临终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见到了我妈妈!”老人的记忆仿佛是夜空中的星星,零零散散,却总有一两颗,在最需要的时候闪烁出光亮。
因而我会想:如果注定要告别记忆,那是否该更珍惜它还在的时候,与那个半依半就的记忆共舞?是不是应该多记点,多写点、对还在乎你的人多说点,以至于变成一个被照顾、被回忆的对象时,心里更安然。学会放慢脚步,把那些微小却真实的瞬间留在心里——一次黄昏的散步、一场无声的拥抱、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丁点微不足道的感悟。这些小小的脑蛋白的涟漪,说不定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是我记忆中最闪烁的星火。
也许,当我们真正与记忆离别的那一刻,我们已然不再恐惧,不再惊惶。正如秋天的树,不再执着于满枝繁叶,安心地等待冬雪覆盖,静静迎接生命下一次的轮回。
告别记忆,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告别,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告别世界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