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暴徒施凶恶性事件|用行政权力管控社会打击得了黑社会吗?
相关文《唐山更多令人发指内幕曝光 |老鼠过分猖獗,绝对是猫出了问题》
《权力失控,远比唐山流氓更可怕 |唐山的黑火,果然四处延烧!》
惠州见义勇为的夫妇,差点被打死
Posted on 四川
ZT https://mp.weixin.qq.com/s/11_lFM8tgrjXMaZYsuW_qw
唐山暴力案引发的风暴尚未平息,广东惠州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一对见义勇为的夫妻,差点被一群暴徒活活打死。
6月19日,凌晨3点。
惠州惠城区华阳工业园附近,一个宵夜店门口,年轻的老板夫妻在门口的桌子上吃饭,吃完就准备打烊了。
突然,他们听见不远处的路边上,有女生呼救,于是宵夜店老板迅速冲了过去,发现一个男子正在殴打一个女生。
案发现场视频截图@魔都囡
店老板在劝阻男子不要打人的时候,一群男子冲了过来,开始围殴劝阻的老板。店老板一边抵挡一边后退,甚至上衣都被扯掉了,被这群男子打的浑身是血。他们用带扣的皮带狠抽店老板,用砖头、凳子,砸破店老板的脑袋。
身穿黑衣的老板娘试图上前保护丈夫,也遭到这群暴徒用皮带、板凳的毒打。
最令人愤怒的一幕是,夜宵店老板浑身是血地躲闪时,有个暴徒拎着砖头,高高跳起,下死手的敲向店老板的后脑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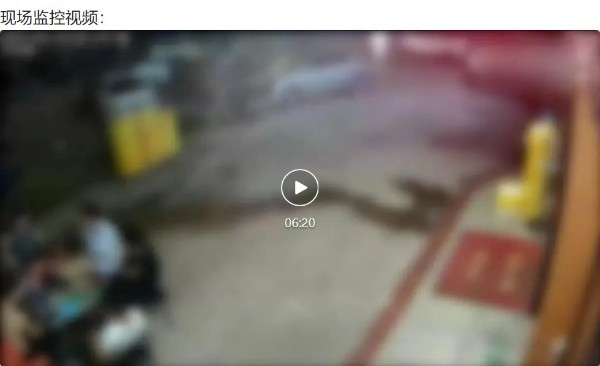
【看视频请点击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11_lFM8tgrjXMaZYsuW_qw】
万幸的是,接到老板娘报警电话的警察,迅速赶到了现场,警察赶到时,还有一个人正拎着刀追杀店老板夫妻。
之后,店老板夫妻因为伤势严重目前正在医院抢救。
6月19日晚,当地警方通报称,主犯洛某龙(23岁)和他的4名老乡均被抓获。
01
唐山事件和惠州事件,如果仅仅看暴力场面,很多人都会以为这是仇恨不共戴天的两伙人在“火并”,手段之残忍,下手之狠毒,令人咂舌。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唐山事件是性侵不成遭遇了女生的反抗,惠州事件是殴打女生遭到了见义勇为者的阻拦。
这显然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可为何却遭到了暴徒们的凶残殴打呢?
百多年前的鲁迅,笔下有个阿Q,他见到赵老太爷会吓得尿裤子,但是转过头欺负小尼姑却毫不含糊。
这就是奴性。
奴隶在赵老太爷、假洋鬼子等面前是卑微的,不敢有一丝的反抗,甚至在比他强点的王胡面前,也只有被欺辱的份。
但做奴隶要嚼出甜头来,品出快乐来,怎么办?
鲁迅在《灯下漫笔》写道,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开始,中交票(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突然就不值钱了,突然他们说,好像中交票可以换银元,但却是接近半价,于是就拿了100元换成了60元的银元。
这时候当人们拿着银元放到口袋之中感觉就不一样了,非常的开心,而且放到兜里沉甸甸的感觉可真好。这样子既安心又喜欢,这样子终于就有了踏实感。
哪怕是吃亏了,仍旧还是开心得要命,鲁迅说这个就是做奴隶了,而且还做到很开心。
鲁迅还说,奴才和流氓,“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大家还记得上面有张图片里,一个光膀子的暴徒,手拿砖头高高跳起,下死手的敲向店老板后脑勺。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手持U型锁,狠命砸向同胞脑袋的蔡洋。
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平时他们给别人当奴才,唯唯诺诺地习惯了,忽然遇到比自己弱的了,欺负起别人就更加残暴,这个时候,他们也是快乐的,开心的。
惧怕强者,欺辱弱者,这不是人性的恶,而是奴性。
02
文明社会的制度本质,其实,就是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对所有人都适用,人们只需要对游戏规则是否公正做判断就可以了。
这套规则是基于人性和良知,源于普通人角度的思考和判断,它能够惩治“恶人恶行”、引导“人心向善”、鼓励“见义勇为”。
如果见义勇为的后果是被定性为互殴,被羁押,被判刑,像赵宇案一样,那么一个社会就将很快走向全面的溃败。
有人会说,唐山事件也好,惠州事件也好,不过是偶发事件,和我们日常生活关系不大。
事实绝非如此。
当我们看见一只蟑螂的时候,那说明看不到的地方肯定还有100只。如果我们视而不见,很快整个房间里到处都会爬满蟑螂。唐山事件后,几十上百起被媒体曝光的实名举报,其实已经证明了这点。
严惩一次犯罪者,比教育一万句受害者学会保护自己有用!
阿Q要是知道捏了小尼姑的脸蛋,会被赵老爷扇耳光,你觉得他还敢吗?
唐山女子被暴打,全社会都在为她们发声。
惠州见义勇为的夫妻差点被打死,难道就不配大家的关注吗?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
许纪霖:黑社会为何屡禁不绝?用行政的权力全面管控社会、打击黑社会行得通吗?
Posted on 北京
ZT https://mp.weixin.qq.com/s/ot3_vvo6OPCoidSCtc6LmA
摘要
只有积极鼓励和发展合法的民间社团,与政府管理形成良性互动,这样才能从根子上打击黑社会,铲除黑社会存在的土壤。即使在某些非常时期出现了短暂的“行政失灵”,政府权力瘫痪,社会也能依靠自身的社会组织网络,维持自发的秩序。如今中国最大的危险在于,社会稳定通通押宝在政府强有力的有效管理上,一旦出现权力失控,社会就会随之大乱。
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建设的大问题,值得认真对待。
托克维尔的启示
秦统一中国之后,虽然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郡县制,但国家权力的触角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镇和村庄,并没有政府的基层机构。两千年的历史当中,不仅乡村如此,城市也是如此。虽然国家权力不下乡,没有深入基层,但在大部分朝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社会的底层还是秩序井然,民众能够安居乐业。个中的秘密在于,在传统中国,有一个相对于国家的基层社会,它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由儒家士绅作为地方精英,实行乡村的基层组织和管理。到了明清以后,不仅乡村,而且城市日常生活的管理也由士绅们来领导,这被称为“士绅为核心的管理型公共领域”。基层社会的各项公共事务,从水利、慈善、消防,到祭祀、教育、纠纷调解,都由宗法家族自己解决,或者由士绅为领袖的地方性“权力的文化网络”自我管理。国家政权的县一级政府,只管理两件大事,一个是收税,另一个是刑事诉讼。古代中国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比起今天要低得多,但因为有以士绅为核心、宗法家族为基础的自主性基础社会的存在,整个国家依然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得以维系着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
中国的乡村自治传统,到了晚清民国时期被逐渐破坏。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一步步深入到基层社会,大量的地方精英流失,乡村的公共事务被各种土豪劣绅把持,国家权力借助他们延伸到基层,鱼肉百姓,搞得民不聊生。中共的农村革命就是在过度国家化的乡村危机背景下爆发的。1949年之后,中国建立的是由国家全面控制基层的全能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才定下“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战略,让社会从国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以恢复现代社会应有的活力。
一个现代的社会乃是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从梁启超、孙中山开始,各家改革人物都将乡村自治和地方自治作为中国复兴和变法改革的重要环节,认为国家的民主首先要从基层和地方开始,在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同时,更要重视地方自治的基层设计。他们的基层设计方案除了来自中国古代的历史传统之外,更重要的是受到美国地方自治成功经验的启发。
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著有非常有名、流传至今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是他当年考察美国民主的思想结晶。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时,带着一串让他百思不得一解的问题:为什么法国1789年大革命血流成河,之后旧制度多次复辟?为什么法国无法跳出民主与专制的历史循环,而美国又是如何在革命之后成功地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的?他在美国周游一圈之后终于发现,美国民主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美国的民主有社会基础,源自英国统治期间13个殖民地的地方自治传统。它使美国人民具有丰富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民主经验,大批的自愿性社团让社会生气勃勃,形成了自发的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又涌现出一批地方自治领袖,美国的开国元勋包括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都是多年领导地方自治的德高望重的精英,他们把地方民主的经验带到整个国家制度的实践上,使国家的统治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托克维尔对此称赞不已,感慨法国因为长期的君主绝对专制制度和官僚统治,导致国家权力过于强大,而社会缺乏像美国那样的地方自治,以至于新建立的人民主权徒有虚名,旧制度的幽灵很容易在新政权的躯壳下借尸还魂。
托克维尔的思考给后人这样一个启示:一个国家的民主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还需要基层设计,否则民主制度就像空中楼阁,其基础是不牢固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民主的试验,民国肇建之初,多党制、议会内阁制、司法独立等一套现代民主制度都有过良好的设计,还一度实践过,不过通通归于失败,结果袁世凯乘势代之以强人的威权统治。民初民主制度的失败,其中一个原因乃是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城市上层的革命,而当时中国的乡村和基层社会没有太大的变化,缺乏地方自治的基层民主传统来支撑上层的民主变革。
民主要从基层做起
民主是一个好东西,这是大家公认的,但究竟什么叫民主,民主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按照经典的释义,民主是通过普遍性地投票选举国家与地方的政治领袖,也就是以普选为核心的制度。这种投票式民主固然不错,但绝非民主的全部内容。民主不仅关乎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也与社会自治的基层设计密切相关。
假如民主仅仅是选举,仅仅是为选举政治精英,那么民主便只具有工具价值,而其他非民主的方式同样可以产生政治精英。真正的民主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这个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生活领域,让公民具有自治能力,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统治的能力。从这个意义而言,地方的民主、基层的民主有时候比国家的民主对于一般民众更重要。美国的总统选举,除非是非常时期,一般投票率不高,国家公共事务对于许多人来说隔膜得很,不一定与切身利益相关,因而往往会造成放弃投票、放弃权利的“公民冷漠症”。支撑着美国民主的核心,反而是地方选举。公民参与热情最高的是乡镇一级的地方选举。乡镇一级的公共事务,比如地方财政是否要增税、纳税人的钱如何支出、学校和图书馆的建设、道路和绿化的改善等,都与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相关,一般公民参与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要远远超过关心国家大事。
美国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杜威说过,民主不仅是一套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在现代多元社会里,人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价值信仰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高度分化的人群,如何“和而不同”、彼此相处、共同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社群之中?这就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领域学会倾听,学会交流和对话,学会和与自己利益冲突的人群交易妥协,学会与不同价值、不同信仰的他人和平共处。这就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很难想象,日常生活的民主可以通过国家的意志、政权的力量或者法律的手段加以推行。制度层面的设计只是为日常生活的民主提供必要的制度平台和法律框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自主性的社会,让民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生长出来,形成一套来自生活世界的政治文化。一个民主的国家,只有在公民之中养成了普遍的民主习惯,倾听、容忍、妥协和尊重他人成了公认的美德,民主才不仅有法律的制度平台,也会有更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
黑社会为何屡禁不绝?
一个自主性的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有各种合法的、活跃的自愿性社团。现代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在市场经济和社会高度流动的冲击下,传统的血缘、地缘社群处于持续性的解体之中,个人离开了传统社群的庇护,被抛到社会上,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化的个人。然而,人毕竟是群体性动物,激烈的生存竞争一方面使人们相互分离、相互对立,另一方面又迫使人们寻找同道,重新组织起来,形成各种自愿性的社团。在强大的国家意志面前,个人再强大,也总是渺小的,个人的价值和利益无法单独实现,因此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与自己的利益、信仰和趣味相近的人,组成自愿性团体,以寻求共同的利益。
当今中国有些地方黑社会猖獗,其重要原因在于:当温和的、合法的民间组织缺席的时候,社会形成了一个秩序的真空,处于原子化的个人需要有安全感,需要去寻找庇护者,于是被迫依附于黑社会寻求保护。那么,回到原来的全能主义手段,用行政的权力全面管控社会、打击黑社会行不行呢?从短期来说,这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但从长期而言,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会抑制社会自身的活力,负面效果明显。不少地区的黑社会甚至与某些腐败官员互相勾结,形成有保护的黑社会势力,反而更加猖獗。社会如同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合法的民间社团是健康的细胞,相互之间会形成自我保护的免疫系统,假如正常的细胞受到压抑,黑社会这类癌细胞就会迅速繁殖、扩散。因此,只有积极鼓励和发展合法的民间社团,与政府管理形成良性互动,这样才能从根子上打击黑社会,铲除黑社会存在的土壤。即使在某些非常时期出现了短暂的“行政失灵”,政府权力瘫痪,社会也能依靠自身的社会组织网络,维持自发的秩序。如今中国最大的危险在于,社会稳定通通押宝在政府强有力的有效管理上,一旦出现权力失控,社会就会随之大乱。
现在有一些官员总是很惧怕民间组织,担心它们会形成有组织的对立面,借维权名义挑战政府权威。这些官员转变执政的思维。即使是一个民主社会,也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冲突。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指出,美国的社会冲突一点儿也不比中国少,但它并没有演化成制度性问题。因为美国有一套政府与社会、社会不同群体博弈的规则,并且已经制度化,但中国目前还没有做到。事实上,当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时候,政府最大的敌人不是有组织的社团,而是一帮乌合之众。因为在采取必要的措施之前,政府总是希望通过沟通和谈判来解决问题。但面对乌合之众往往找不到谈判的对手,即使对方推出临时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也很容易被激进的群众所否决。一批没有组织的群众,谁越激进,调子越高,越是会成为新的群众领袖。因为乌合之众总是希望一次性获得最大的利益,因而很难与之对话和谈判。因为乌合之众缺乏理性,自身又没有组织,所以群体性事件往往会演变为暴力性质的打、砸、抢。
但有组织的群体就不一样了,他们具有自我约束机制,很少会诉诸暴力,而且追求的是长期的、稳定的利益,派出的谈判代表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政府比较容易与他们达成妥协,达到相互利益的妥协和平衡。
一个法治国家不仅需要理性的政府,也需要理性的社会。这个理性的社会,要有发达的民间社团和成熟的草根领袖。在传统中国,儒家精英就是民间的草根领袖,他们在民间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而且能与政府形成良性的互动,一方面代替政府管理民间社会,另一方面又代表民间与国家进行理性的政治博弈。传统中国的各代王朝管理成本不高,但效率未必比今天低。到了民国之后,现代的市民社会在不少城市特别是上海有可观的发展,从袁世凯死后到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曾经历了十多年的北洋军阀混战。在政府如走马灯一般轮换的乱世之中,维持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都会的,乃是一批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民间领袖的地方自治力量,而支撑地方自治的,正是多元、发达的民间社团,比如商会、银行公会、教育会、律师协会、记者协会、会计师协会、工会等,它们形成了地方“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些地方网络正是培育草根精英的最好土壤,而政治的民主化正需要这样一批来自底层的精英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