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怀澄:归国记④在劫难逃
1957年我在晋北大同市任职,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我移居大同还不足一年。那一年秋,上级宣布,我任职的单位迁往大同,在大同成立公司,在“党叫去哪里就去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的年代,没有选择地便从首都也是古都的北京迁到了更加古远的古都大同。
大同位于山西的北部,与内蒙古相邻,是中国北方的历史名城。公元398年,北魏建都于平城,便是后来的大同。
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在西门外,办公室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农田,种的是土豆,土豆是大同的主要农产品,食堂也常以蒸熟的土豆作为主食供应。我分到了一间半的住房,花了不少时间收拾,在打磨地面上结块的灰浆时,一直在琢磨着到底要不要把妻儿接来。思考的结果是否定的。儿子早产,体弱多病,是北京复兴门外南礼士路儿童医院的常客,每月必去医院报到的。大同的医疗条件怎么能与北京比?大同的冬天又比北京冷许多,尽管有笑话说小便要随身带根棍子打是过分夸张,但一口痰吐到地上立马冻成一块冰却是事实。多病的孩子怎么适合到大同来?我作出决定,把清理好的住房退回,搬进集体宿舍。
1957年初,我给建筑工程部人事司写了一份报告,除了说明孩子多病需要照顾外,我提出我学过新闻,最向往的工作是编辑采访工作。我的请求很快得到人事司的恩准,一面将调令下到大同,一面通知北京的建筑出版社,将调来一名编辑人员。建筑出版社一位行政人员是我们的邻居,接通知便告诉我妻子,早早把办公桌安顿好,只等我到任了。可惜,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一直没有露面,我的愿望搁了浅。
是什么使我的愿望成为泡沫的呢?命运捉弄了我。就在我的调令抵达大同的同时,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文件也抵达大同,公司把调令压住,反右斗争开始。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的人生在1957年的关键一刻不能自制地滑入了一条沟壑。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反右派斗争开展不久,《大同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条新闻:中央驻大同市某公司揪出右派反党小集团,小集团成员4人,我的名字在4人之中叨陪末座。突然见报的事态发展如晴天霹雳。在《大同日报》的新闻发表之前,在计划科的学习会上,并没有批判我,并没有指出我有什么右派言论,更没有指我是右派分子。这真是不可思议,一个人的命运竟然可以被任意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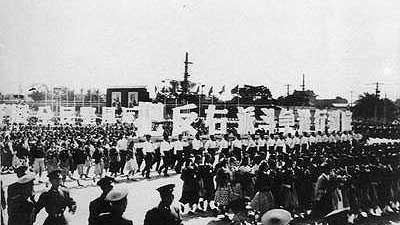
人受到突然打击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平日一样走进办公室,和平日一样拿起报纸,突然看到头条大新闻把我和另外3个人一起钉上了耻辱柱,那一刹那,我感到一桶凉水从头顶灌下,大脑好像冰冻了一下,麻木了一阵,然后才慢慢恢复。这种凉水灌顶的感觉,我一生中有过两次,一次在1955年的肃反,一次在1957年,都是60年前我年轻时候的事了。
60年前发生的事情,对我的打击不是时间可以治愈的创伤,不是失之东隅的损失,也不是塞翁失马的不幸。在“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政治上的污点是终身的,是世袭的,是无法改变的。在“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年份,尽管对右派宽大为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处理是处理,性质还是敌我矛盾。
人在绝望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父母亲人、老婆孩子,痛苦中特别想念他们,但他们都不在我身边。
我的妻子带着多病的孩子,日日盼着我调回北京的好消息,可是我现在要告诉她的是截然相反的坏消息。我真没有勇气告诉她,但又不能不告诉她。写了一封颠三倒四的信,那不是舞弄文笔的时候,也不是倾诉委屈的时候,说得简单明白点只是一句话,我被划为右派了,可是怎么能像电报一样,一封倾诉苦难和委屈的家书只有一句话呢。不管怎样为难,这可怕的家书还是塞进了邮筒。
妻子的回信来得很快。她宽慰我,她说都是那小集团的其他3个人害了我,她表明不会抛弃我。我知道她受到的打击一点不比我受到的打击轻,她在读信的一刹那,一定也有一桶凉水从头顶上灌下来的感觉。这是她因为我受到的第二次打击,发生在1955年的第一次打击是虚惊一场,发生在1957年的第二次打击却是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的打击产生实实在在的后果,妻子后来面对的重大问题,都实实在在地与这实实在在的打击有关。一年后中央各部精简机构,领导对妻子说:你愿意留在中央工作呢,还是愿意下放到地方去?不过想要留在北京,必须与你的丈夫划清界线。划清界线是离婚的同义词,妻子不能回答说我不划清界线,只能说服从组织分配。好心的领导给妻子三个地方作选择,安徽的合肥、浙江的杭州和广西的南宁,妻子选择了南宁,因为我服务的公司迁去广东茂名,两广相邻,靠近一点吧。后来在南宁,领导对妻子说:你工作很出色,各方面都好,但是,你申请入党,最要紧的是要与你的丈夫划清界线。妻子不能回答说我划不清界线,只能说愿意继续努力。妻子铁了心当右派的妻子,说实话是没有什么盼头的,不过她还是盼着,倒也没有完全使她失望。
后来盼到了摘帽子的好消息,我从广东打一个电报到广西,这次电传家书只用一句话,妻子至今珍藏着发了黄的1960年的电报纸。后来又出乎意外地盼到了改正的喜讯,我错当右派,当然她也错当右派妻子。再后来错划右派的人变得吃香起来,右派代表着说真话办实事,尽管是很虚的事情,妻子也乐于听到这类不像恭维的恭维。
我的父母在香港,辞别父母的时候,父亲说这样也好,大学毕业回香港来,再去美国深造。回上海进了大学以后我变了,一再写信告诉父母,毕业后留在国内不回香港了。
在父母的眼里,儿子真的被共产党洗了脑。后来,我又突然一下子转到了革命的反面,父母会怎么看待呢?从1955年肃反后开始,我中断了与父母的通信,父母通过与祖父、大伯通信知道我的情况。1957年的夏天,我好像是被风吹折的小树,父母无力把折枝扶起,让它重新茁壮成长。天下的父母最伤心的是对子女的沦落无能为力。
我对自己的沦落想不通,深感孤独,深感无助。犯罪的人在进行犯罪活动时是知道正在犯罪的,贪污犯贪污,强奸犯强奸,杀人犯杀人,间谍进行间谍活动,反革命进行反革命破坏,他们都知道正在做的事情是犯罪的,知道犯罪而进行犯罪,罪有应得。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在犯罪,为什么定我有罪呢?即使说错了话,不还有“言者无罪”的一条吗?世上没有人不说错话的,为什么戴着有色眼镜盯住我呢?不公平啊!
共产党有句很感人的名言:革命不分先后。论先后,我是后了,不过,我是自己走到革命队伍里来的。我听我的叔父、我的朋友讲新中国好,我放弃去美国读书,我来了,应该欢迎;我来了不走了,应该爱护。对国外回来的人,首先要看到回来这一点,这就是进步,就是爱国。可惜有许多爱国之士从国外归来,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新闻界前辈马国亮在香港被港英政府驱逐,指他是左派;他回到国内,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这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我只能消极地思考,真的在劫难逃吗?
如果命运不是有意捉弄我,早一个月离开大同,到了北京的新单位,周围的人都是初相识,或许可以避过一劫;如果大学毕业我留在上海,上海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大把抓,或许可以避过一劫;如果大学毕业我回去香港,当然避过一劫。
右派分子这顶帽子,视之无形,顶之千斤。帽子批发店里又把这顶帽子和“地富反坏”的帽子放在一处,更使被扣上帽子的从来清高的知识分子大受屈辱,愈发觉得这顶帽子的肮脏龌龊,见不得人。
我在戴着帽子和摘去帽子但帽子还拿在别人手里的年份里最不愿见人,尤其不愿见生人。知识分子死要面子,得了帽子,丢了面子,这便是持久痛苦的原因。
右派分子的帽子使戴上了的几十万知识分子至少痛苦了20年。
我是在隔了许多年以后,一位正直的共产党员、我的妹夫盛斯猷对我提起“阳谋”“阴谋”之说。那时我已经摘掉帽子,当时对他告诉我的事情没有多想。后来99.98%的右派都改正了,说明当时中国没有所谓的牛鬼蛇神,没有所谓的毒草,牛鬼蛇神或者毒草是人为制造的。所以不是阴谋还是阳谋的问题,而是人为制造一大批牛鬼蛇神的错误政策的问题。
领导圈定某人是右派,此人便逃避不过去,随便你说什么,都可以划为右派。由中央到省,由省到地,由地到市县,文件通知的下达,需要时间。4月27日中央指示整风,我服务的公司开始整风是在5月份了。公司的整风运动平和地开始,第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是哪一天召开的记不得了,事前我得到通知要参加座谈要发言,我很认真地准备了讲稿。我的发言内容是关于肃反运动,对被隔离审查5个月有意见,但我的发言一开头就强调了全国肃反运动的成绩。我的发言自然成了所谓的右派言论,其实我的发言没有错误,很实事求是,可是整理材料的人可以断章取义,歪曲原意。
复查改正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在肃反时,组织认为程怀澄从香港回来,被列入肃反对象受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某些办案人员存在着不符合政策的做法,程怀澄对此思想不通,有意见,发了一些牢骚,他在五七年座谈会上发言时说:我认为肃反运动是伟大的,基本上是健康的,人民都会拥护的,中央的方针政策是英明的。可见他对整个肃反运动是拥护的,而仅仅是对本单位一些做法有意见,并非攻击肃反运动。”
谢天谢地,我的座谈会发言稿还保留在我的档案里,使负责复查改正工作的人很容易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我只是对本单位一些作法有意见。具体地说,我是对负责审查我的程苏有意见,此人出身地主家庭,隐瞒身份,文革中被遣送原籍,不久便死去,可谓“天谴”。
从1955年8月1日开始,隔离审查我5个月,除夕领导对我说:“今天你可以回家了,你没有问题。我们共产党讲任劳任怨,任劳容易,任怨不易,希望你正确对待这次审查。”肃反运动中并没有给我作结论,或许我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不必作结论,我当时也不懂结论的重要,可是经办人把审查中所有不是问题的问题都装进了我的档案。
光靠座谈会上的发言是不能定我为右派的,于是不择手段地用了在肃反中审查过而且否定过的问题,当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一案已经被黄嘉德教授否定了,还是作为主要罪状加在我的身上,办案的人真是下流到了极点。
所谓右派言论有的简直幼稚可笑。有一郭姓同事吸烟,原抽恒大牌,结婚后改抽较廉价的烟。我笑话他说:你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一塌糊涂。郭竟揭发称程怀澄说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得一塌糊涂。检举人可以是低水平,办案人也可以这么低水平吗?
我在反右检查中交代的错误思想也成为右派言论。更有甚者,还有的话我没有说过,也作为我的话来诬陷我。复查改正报告对这类无中生有的诬陷指出:无凭证,不落实,应予推倒。无凭证不落实的东西也入罪,使我感到办案人员是不择手段,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在政治运动中,最可怕的就是这类人品不端、办案不公的人,这类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犯的是诬陷罪。闻名全国的“大右派”葛佩琦,因为一句“要杀共产党人”而成为千夫所指,可是事实上葛佩琦并没有说过这话,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刊《人大周报》不负责任的捏造,《人民日报》原文转载,葛佩琦多次申诉要求更正,《人民日报》置之不理,葛佩琦为此坐18年的冤狱。这就是诬陷,害人不浅、不负责任的诬陷。
这些诬陷者有的还活着,又有多少人会勇敢地站出来呢?
1957年定我为右派的文件,并没有给我看,没有我的签字。如果当时给我看了,我是会提出不同意见的。不给我看定案材料,是办案人员的故意。1979年的复查改正报告给我一份,我保存着,通过复查改正报告,我才知道当年东拼西凑合成的罪证,是多么地罔顾事实,蔑视法理。如果不改正,岂不冤枉人一辈子。
东拼西凑的罪证中分量比较重的是关于反党小集团的内容。在中国的政治术语里,小集团是反革命组织的雏型。历次政治运动,都有反党小集团被揪出来,而且一旦成了小集团,其罪过就要比单枪匹马严重得多。反右一开始,把章伯钧和罗隆基定为章罗联盟,实际章罗二人水火不容,一贯不和的,何来联盟呢?既然有章罗联盟作为样板,也就依样画瓢,把几个人放在一起可以定为反党小集团。
我们公司的所谓小集团成员4人,另外3人是何士达、左琥贞和鲍德芳,3人均为机械工程师,年龄均比我长许多。我是到了大同才认识他们的,工余时间常聚在一起打桥牌。大同古城,业余消遣娱乐的地方几乎没有,打桥牌成为我们工余唯一可打发时间的活动。牌友除4人外,还有一位总工程师张显庭,张是党员,为人正派,工作特别负责,我们都很尊敬他。每次打牌都在鲍德芳家。鲍是杭州人,我的同乡,每当打牌他的妻子就忙于为我们沏茶添水,又常把家里蒸的窝窝头放在炉上烤了飨客,虽是粗食,大家也当作美味吃。除了打牌,从不相聚,打牌时很专心,也不谈论其他事情,小集团活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如果有小集团活动,最能发现问题的是总工程师张显庭,为什么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打牌而没有任何举措,为什么反右以后他不揭发呢?我相信关于小集团一说,张总也是不认同的。
既有小集团,总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说我们是妄想夺机械科的权,这更是无稽之谈。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个人要夺权,怎么夺,夺什么?不是吃错了药吗?再说我那时想的是调北京做采编工作去,打牌消遣,哪有别的心思。可是祸出桥牌。
我服务的公司揭露反党小集团,一举揪出4名右派分子,反右斗争旗开得胜,向上级报告战果,不料上级说还没有达到指标。于是公司又召开第二次知识分子座谈会。第二战役的战果也不错,又揪出3名右派分子。3人中一人是我的同科同事,前面提到过的郭庆生,他曾经把日常谈话中的小事无限上纲揭发我,现在轮到别人这样对他了。第二次知识分子座谈会前夕,他在办公室说:通知明天参加座谈,担心说错话,可是又不能不参加,参加了也不能不发言。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果然中箭落马。其实点到他的名,已成箭靶,说什么、怎么说都一样,在劫难逃了。
三人中的另一人姓周名洪波,天津人氏,参加过赴朝志愿军,退役后来建工部系统,因无专长,在行政部门办些杂务,怀才不遇,时有牢骚。周氏亦被邀参加座谈会,公司人事科张步尘科长与周氏之兄在军队是亲密战友,科长出于战友情谊事前约周氏谈话,叫他言论多谨慎。周氏视作耳边风,买醉后出席座谈会,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结果未能逃过一劫。第三人姓张,此人情况不详,张氏和我都是共青团员,后在同一个团的会议上被宣布开除团籍。
公司的右派,4加3等于7,这个数字已超过5%的指标,反右斗争也就到此结束。在经济领域,指标是提出目标和检查成果的有效手段,可是在政治思想领域,也能用指标来硬性规定目标吗?有笑话说,某大学的一个党支部,缺一人未能完成反右指标,一贯以身作则的党支部书记就自愿填补这名缺额,真所谓舍身饲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