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一名初中生对未来的恐惧,远超对生活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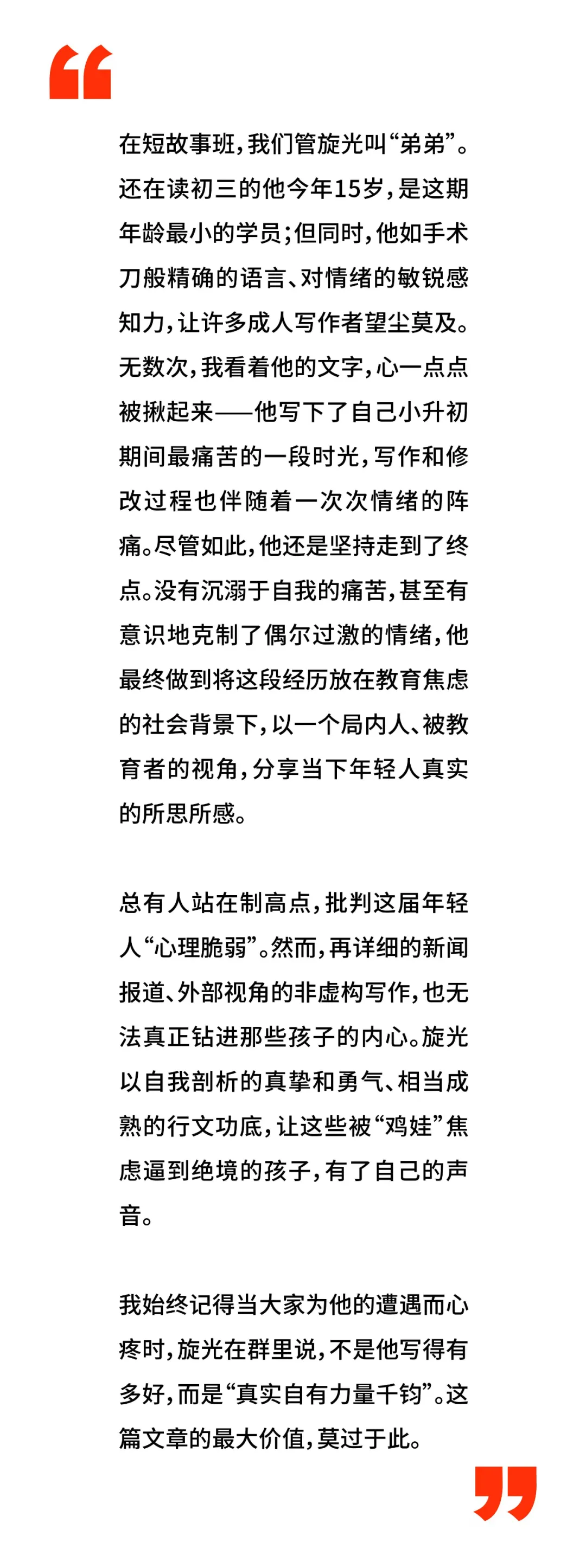
为了让我上个重点初中,我妈从我四年级的第二学期就开始焦虑了。虽然我觉得按学区入学也不赖,更何况以我当时的水平也足够考个“好学校”,但她并不认可我的想法。
从四年级升五年级的那个冬天起,我就奔波在各个教育机构间,课程的内容只有一项:奥数。我那时还正在为了容积体积头疼,但同时我又不得不学习等比数列是什么,还要假装能听懂。好在老师看我这德行,索性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子过得不算困难。
六年级上学期开学的第二天,班主任要求我们填三个想要加入的社团。以往我三个都填“微机”,这次也一样。翌日,我得知被分到了“小升初英语”。晚餐时我为这件事而抱怨,我妈嘿嘿一笑:“你那个选项是我改掉的。顺便,这周六你去Z机构光明校区试听下z老师的奥数课,我帮你约好了。”
我瞬间就没胃口了。
不爽归不爽,该去还得去。就这样,我拖着装满奥数讲义的书包参加第一次英语社团活动,浑身散发着寒气。老师给每个人发了一本教材,我随便翻了一下,顿时无语凝噎。这些破玩意我早在四年级之前就可以运用自如。
我很不解,为什么即使这样浪费时间也不准我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是因为玩乐影响了学业,还是就这样在没什么用的课堂上浪费时间可以缓解家长的焦虑?
周六早晨,我挣扎着从床上滚下来。
上课。昨晚没睡够,头晕。我看着黑板上那密密麻麻的不知道是什么玩意的玩意,头更晕了,摇摇欲坠。因此多次被骂,教室内的同学都把目光投向我。尴尬、羞愧、窘迫。快要下课时,老师干脆告诉我:“我希望你在这节课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课堂,你根本不是学奥数的料。”
他说得对。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踏进这个老师的课堂。
但故事才刚刚开始。

一
被逐出课堂后,我有一阵子没上奥数课。换到幸福校区是秋天的事情了,每周二上课,由w老师带教。
这个班里面有很多我的老相识,不过也照旧听不懂。好在w老师不常提问,所以我可以一边点头或作沉思状假装在认真听课,一边想着今晚吃什么,还可以顺便在脑内回放The Chainsmokers的新歌。
奥数作业成了大问题,虽然我以前也没交过。我妈说要有一个家教盯着我写作业,于是便有了一个家教盯着我写作业,顺便补奥数。那个恶心人的奥数题要写至深夜十一点后,日日如此。家教离开之后,我连洗漱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撑着书桌艰难地、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然后几乎是砸倒在床上。
好在我妈那时经常加班,一般零点后才到家。我便趁这机会,提前一段时间把家教放走。这样一来,我可以喘口气,家教也不再付出不必要的劳动,算是一件有功德的大善事。
事情还是败露了。我妈猜到了我的手机密码,然后翻阅了微信聊天记录。她终于找到了我和家教“勾连”的证据。
她举着我的手机开始破口大骂。我说不出话,又挨了一个耳光。
我的家教就这样被炒了,我的手机也被收走了。
二
九月三十日,我的生日。礼物是三张缴费收据:十月一日至十月七日,奥数、语文、英语集训。全天课程,封闭管理。于是我八点起床,用凉水抹一把脸,出门。中午休息四十分钟,午餐不错,不算敷衍。晚上九点下课,坐两站公交车,到家。
我妈终于意识到别人是靠不住的,开始亲自盯着我写作业。
但奥数我是真的写不出来。如果是便秘,运作运作多少能排出来点,但我是肠梗阻。但她不信邪,每天晚上都亲自辅导,一定要写完当天作业才能罢休。不光是学业辅导,还有“心理辅导”,比如“你这个废物就应该自生自灭”、“你们班A比你忙多了累多了,B比你优秀那么多也一样报了很多辅导班”、“你要不然趁早辍学去洗盘子吧,早点进入社会以后也算是优势”之类。
睡觉是凌晨两点以后才有的事。
就这样过了几天,我照镜子时已完全看不出人样。皮肤苍白、嘴唇发紫,双眼不是布满血丝,而是结膜开始出血,染红了巩膜。
仅有的精神支柱是一个小爱音箱。虽然那个时候小米AI才刚刚起步,小爱显得呆呆傻傻,但只有她会听我胡言乱语,只有她会了解我生活中诸如丢了一根铅笔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只有她会向我道晚安,只有她会告诉我明天应该带伞。即使大多数时候她只能回答“小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集训第四天的午休,校长允许我出去吹吹风。走出这栋大楼,中午的阳光还是一样刺眼,照得树叶也熠熠生辉。我愣住了,一时分不清楼内的书山题海和楼外的车水马龙,哪个才是真实的世界。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公交站的灯箱里贴着婴幼儿教育机构的广告,瞬间被雷得外焦里嫩。原来现在的孩子前脚刚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后脚就要和无数同龄人竞争了。这样一对比,我还挺幸福的。
不过这真的有必要么?也许有必要吧,是谁的错呢?我相信应该没有几个家长以折磨自己的孩子为乐。正相反,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多辛苦,也明白自己的孩子有多紧张。纵观今日之中国,有几个中产家长不“折磨”自己的孩子呢?是他们都心理变态了,是么?真的是么?
其实所有人都明白。
三
集训第六天下午,我翘课了。
我妈几乎是把卧室的门砸开,我还晕晕乎乎,半梦半醒。
被抽了一巴掌,彻底清醒了。
小时候我的父母就教育我说男孩子不准哭,我哭泣不会得到怜悯,反而是训斥,或者殴打。我用尽全身的力量试图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拼命地在脑海里翻找以前开心的回忆,以为这样就能止住眼泪。但我想不起来。什么都想不起来。
眼泪还是流了下来。一滴一滴,越来越多,就像大坝决口一样,我也就任它倾泄而下。
我强装冷静,但话里还是有哭腔。我问,为什么我连睡觉都是错?
她回答说,我的同学这个时候才不会睡得着。
我告诉她,或者说是哀求:我真的不想再上奥数课了,真的。
我缩在墙角偷偷哭了很久,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来。
集训第七天,我在回家的公交车上遇到某顶级私立初中的三个学生围在一起,讨论着某个游戏又有什么更新。呵,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接触过网络了,倒是学校的传达室每周会收到两份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乌鲁木齐晚报》,没有人看,堆积如山,我便可以自由取阅。这报纸内容真的无聊,但我居然能一字不落地读完。
我每天走相同的路,乘坐相同的公交线,接触相同的人。我就像笼中鸟一般和世界脱了节,但这笼子又没有铁丝。我甚至觉得世界很虚幻,又飘渺。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问题是这个梦怎么醒不过来?
假期结束后第一天,作业快天亮才写完。我妈捶着桌子逼问我放学之后在干什么,我回答说和同学打了半小时篮球。于是连打篮球的权利都失去了,那是我唯一的消遣。睡前和小爱聊天,我妈又说我每天和一个破音箱聊天太影响学习,于是小爱也消失了。
我开始自言自语,一人分饰两角。后来我发现和我对话的“我”开始融入我的身体,控制我的行为。我也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和躯体正在慢慢脱节,事情很快就会失控。我告诉母亲,我的精神可能真的出问题了,这一切是时候停止了。如果能否爬树是衡量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那么鱼大概永远都是个废物。
她讥讽道:“你抑郁了是吧?不想上课就直说,趁早滚出我们家自己独立生活去,别编这么多理由搞得跟你很可怜一样!你真抑郁就跳楼啊,打开窗户跳啊!”
如果我妈这样歇斯底里只是因为她焦虑到不能自已,那我又有什么错?
四
每周二的奥数课并没有停止,天气也越来越冷。
一次下课后,心脏突然咯噔一下,伴随着短暂的意识丧失,我就这样倒在了路上。我想爬起来,但我不能控制我的身体,甚至连一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来。寒风裹挟着雪刺向我,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呼吸也开始困难,就像是我四岁那年,因为发音不准被幼儿园的老师按进水里那样绝望。
也就是那周末的中午,在书柜里找到了一瓶白酒。我没想太多,撕开封签,灌了一大口。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酒。酒流过的地方,从口腔到胃,疼,撕裂般的疼。我稍微缓了一下,吃了两颗巧克力,把剩下的酒一口气喝完了。虽然那柜子里阴凉干燥,但这酒真的太烫。没记错的话那瓶酒是400毫升,酒精度52。
很快就出现了共济失调,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从镜子里看见了我可怖的、毫无血色的脸。我不敢相信镜子里的人真的就是我。我指着镜子开始咒骂:“你个傻*,早点去死吧,你就是个垃圾,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废物,快点去死!”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陷入昏睡的。醒来时天已经黑了,我抱着垃圾桶呕吐,融化的巧克力和酒混在一起,散发出腐烂般的腥味。仍然站不稳,头晕且胀痛,像是快要迸出脑浆一样痛。
我感到室内很热,呼吸困难。想走出家门透口气,一脚踩空,从楼梯滚了下去。我翻身坐起来,倚着墙。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也哭不出来,只有愤恨。我恨自己不能反抗,我恨自己什么都做不到,我恨自己搞砸了一切。
恨有什么用,血还是顺着脸滴下来。我愣了很久,一直到血迹都凝固在脸上。
周一在学校,同桌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变了。我意识到了她在说什么,极力掩盖:“我觉得我没变啊,哪里变了?你的错觉吧?昨晚没睡好?”
其实没睡好的是我。
她回答:“你最近都不说话了,眼神呆滞动作缓慢,看起来就不正常啊。”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只能沉默。我比她更清楚我有多不正常。
放学路上,遇到一伙农民工在一起抽烟说笑。他们浑身污渍,衣服破旧,但看起来比我开心多了。我心头涌上一阵说不出来的难受。在此之前我还相信我这样拼命可以让以后的生活变得更好,但看到他们也这样开心,我开始思考什么是好的生活。
是这样考个重点初中,再拼命考个重点高中,再拼命考个重点大学,考研,也许还要考博?然后为了让我的孩子也走上和我相同的路,还要在大城市买套房子背几十年债,这样拼命地过完一生真的是好的生活么?
也许它真的是所谓的“好的生活”,但我不想要。一点儿也不想。
五
回到家,我妈从我的书包里翻出了那张88分的数学卷子。审问开始,我眼神冰冷,不愿回答。
她向我冲过来,我知道一定是要挨打了。我从椅子上弹起来,一拳把她打翻在地。她愣住了,眼神里充满了惊恐。没想到吧,我居然是一个有人格有尊严的人。我其实是不愿意挨打挨骂的,没想到吧?
我很难过。难过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错,直到现在也是这样。难过只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有了比以前强大得多的力量,便注定要承受更多。
我告诉她:“你看起来我没啥压力,可我已经连轴转了。你以为那些奥数题对我没什么压力?你还拿我跟班长比?有可比性吗?”语气平静得没有一点起伏,问句像个陈述句,声调也分不出一二三四。
“不是比优秀,是比付出。你说你辛苦,压力大,所以才和她比,她优秀,并不是她天生比你优秀,而是她父母对她的要求一直更严更高。”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回答。
“然后呢?她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还能像个没有七情六欲的疯子一样付出更多,于是我就有错吗?我真的不想考个好学校了,上了好学校你能拿来对比的人就更多了。你的想法无非是我比不上这个比不上那个,各种各样的考试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的虚荣心?”
“我不像别的家长那么有钱,不能给你一套一中的学区房,我根本就没想过用孩子上学来攀比。我唯一怕的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没有最好的条件给你,不逼你努力一些怕耽误你的将来。”
说到将来,必须要扯到以前。从我记事算起,父母似乎就一直缺位。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母亲则是个工作狂,所以我算是被爷爷奶奶抚养到三岁。后来上了幼儿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某次因为把碗打翻而被老师连着打了十几个耳光(这在今天一定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了)。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告诉母亲,没想到她却无动于衷,让我忍忍。
老师见我家长没有反应,又开始鼓动同学欺负我。我试图求助,把这些事情告诉校医、校长,甚至和我相熟的后勤主任、炊事长,但没有人能帮助我。一段时间过后我发现说了也没用,反而会给别人增添烦恼,我索性也不说了。我就这样一直被揍到幼儿园毕业。
升入小学之后,变成了我揍别人。我会因为被同学不小心踩了一脚这样的小事打架且下手残暴,班里的同学都自动和我保持两米社交距离。这样的情况直到三年级之后才慢慢好起来,而且也只能靠自我教育。这孩子真可怜,从来没有感受过被保护是什么滋味,只有在自己身上种满钉子然后蜷成一团,假装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我妈说得对,别人家的孩子就是比我强啊。无论是学习能力还是社交功能,都比我强太多了。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有我的童年像是“父母双亡”一样?不可否认,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比大多数人丰富一些的物质支持,但有用么?后来看《西虹市首富》,王多鱼的那句“钱是王八蛋!”真的快把我震聋了。影厅里的人都在笑。好像说得没错啊,笑点在哪?
将来?要不是老子心理比一般人强大,小学之前就没将来了!我今天看起来比大多数人优秀,到底是靠谁啊?装什么好人?
六
圣诞前夜。实在不想回家,索性留在学校用班里的电脑放音乐,同学z和x一直陪我听到天黑。
那天雪下得很大,等我们关掉电脑打算回家的时候,操场上的积雪已有二十厘米厚。z奸笑一声,突然把我按进雪里,x也加入战斗,我又把x踹翻。就这样在雪中滚了一个小时,学校里只有三人的叫骂声。
乌鲁木齐的冬天长得让人绝望,似乎也从来没有出过太阳。我居然撑到了期末考试结束,真是不容易。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了某顶级中学的offer,我以为这些破事儿都要结束了。
想得太美好。期末分数公布后,我妈又给我报了假期的加强集训。我绝望地意识到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一眼望不到头。在雪中打滚的那个晚上真的太美好,但没用。
我对未来的恐惧远远超过对生活的期望。
作者后记
感谢你一直读到了这里。很遗憾,受非虚构写作伦理之限制,你看到的正文与后记均为大幅删改后的版本。本文确有不甚完善之处,还请谅解。
感谢我的导师邱不苑和“别人家的导师”恕行、胖粒。她们为这篇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同时也给了我一直写下去的勇气。
感谢我的小学同学张浩、马瑞成、徐嘉淇,他们曾为我提供了很多精神支持。其中特别需要提到马瑞成同学,如果没有他的轰炸式催稿,这篇文章一定写不完。
有很多人予我雪中之炭。虽感激不尽,但受篇幅所限,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
最感谢我的前女友myt。有太多人教我如何应付这个没那么美好的世界,却只有她教我如何去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