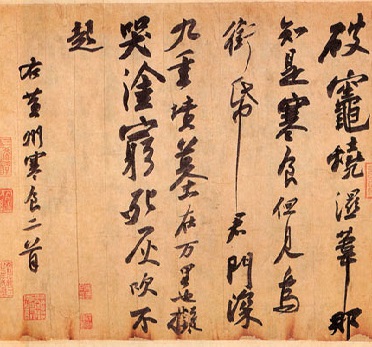无罪的邪恶
小说:
无罪的邪恶
我在一条崎岖山路上吃力地行走,浑身是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走,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只感到脚在不停地移动,身子沉重得很,热,闷,渴得要死。路边除了光秃秃的岩石,什么也没有。我看见前面有一群人,二十来个,围着个圈子在看什么,他们的模样好像都很熟悉,我也围过去。他们在看一只青蛙,一只剥了皮的青蛙,躺在干燥的碎石地上。青蛙的肌肉像淡红翡翠,健实透亮,心脏还在跳动。有人用细竹棍刺它的大腿,青蛙蹦了起来,又落回原地,肛门处流出绿色的粪。突然,围观的人都转过头来,睁大眼睛看着我,啊,是你们!我惊醒了,感觉到紧裹在身上的尿不湿里有东西泄出,温和而潮湿。我盼望阿珠快进来,但我知道她不会来的,此刻她正和她的相好在客厅里咯咯地打笑。
这屋子好空,好大,我像一具僵尸一样躺在这里,有多久了,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还记得。这里是我儿子在上海的家,他离婚后,我就搬过来,那时觉得这房子豪华得都不敢进。他说,爸,你不要走了,我也不再娶了,我们俩人过。什么俩人,他应该说三个,另一个是他的公司,那才是他割不掉舍不去的。为了那公司,孩子老婆都可以不要。他的公司在苏州,老婆是上海人,哪里愿意到苏州去居住。于是他每个月末回来一次,只呆两天就走,准时得像定时闹钟,换了我都得和他离,钱多是用来干啥的。后来他一去苏州,这栋豪宅就甩给我,雇人做清洁,整后院,都是我的事,一搞就要半天。人太寂寞,就喜欢有人来,不管什么人。那天我帮清洁工一点忙,一脚踩滑,仰面摔在地上,后脑撞着楼梯。我以为我死了,谁知道还活着。从家到医院,又从医院到家,最后躺在这里,比死还难受。我的耳朵能听见,眼睛勉强能看得见,有进食的功能,大脑似乎还好使,除此以外,就是一堆衰老的皮肉摊在这床上。全身动不了,声带完全不能发音,我不知道医生诊断什么病,还能活多久。我不想知道。我希望他们停止给我喂食,让我死掉算了,但我连这句话都说不出来。照看的人一天天都在换,儿子一直陪在旁边。有一天,儿子嘴巴贴近我的耳朵,说,我有将近两个月没有去苏州了,现在必须要走。找了一个阿姨来管你,罗总介绍的,靠得住。我付的工资是她要的两倍,她会好好待你的。我眼皮眨了两下,表示知道了,我还能做什么呢?他起身走了,又回来凑近我的耳朵,小声说,她很漂亮。
她就是阿珠。我真想告诉人们,不要以为你有什么幸福的家庭,孝顺的儿孙,每个人到头来都注定要和一个陌生人呆在一起,几个月,一年,几年,看你的造化。我清楚得很,从今后,我这点可怜的生活,如果还能叫生活的话,完全握在阿珠的手里。所幸的是,听见了儿子临出门时对阿珠说了一句话,我有办法知道你怎样对待我父亲的,这使我的心稍稍放宽一点。
我一直在寻思,为什么儿子要回过来说阿珠漂亮,看上了她?这种可能性大概不存在,他和前妻那样的美人都过不下去。是不是想让我开心,放心,人们不是说,漂亮的人使人愉快,漂亮的人心也好。
我先是从耳朵里和皮肤上感到了阿珠的美好。那是软底布鞋轻踩地板的柔声,缓缓地停在我的床前,我感觉被子的一边腾空起来,那样慢,没有一丝凉风窜进,然后被子飘到了一旁。一双不大的,温暖软和的手在我腰背和臀部的位置插进我和床单之间,我的身体被轻松地翻成侧卧。摘除旧尿布的手法很讲究,一只手轻按在粘结带的一边,一只手缓缓撕开另一边,一点没有拉扯的感觉,然后感到有温暖的湿毛巾轻吻我的胯间,松软新鲜的纤维很快复盖上来。接着是富于弹性的双臂托住我的腰和臀,把我还原到最初的位置。那双手连续无间断的运作,像演奏乐器。我僵硬无趣的躯体似乎有点活了。
接下来,一只温暖的手伸到我的脖子下,垫高枕头准备给我喂食。透过只剩一条窄缝的老眼,我看到了阿珠。她算不上影视中那种佳丽或美人,但无疑是阿姨这个行当里的姣姣者。马尾辫掠去她了额上和腮边的游丝,看去像30冒头,杏仁大眼,脸红扑扑,体态健硕,一身朝气。看到她,我似乎也有了点精神,尽量配合着她的动作进食,一改以前在几个看护面前半死不活的模样。
夸大心情对病情的影响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厢情愿。阿珠的精心照料并没有使我的病情朝好的方向发展,这可以从儿子回来时逐渐增涨的焦急不安上看出来。我不知道他此时是几个星期回来一次,但感觉得到他对我说话一次比一次温和,看我的眼神却一次比一次绝望。有一天我躺在床上,似梦非梦地觉得儿子和阿珠在我床前说话。
“你知道霍金吗?”儿子小声问阿珠,不管是不是对牛弹琴,不等待回答,他自顾自地抒发心中的难受,“我爸的病看来只会像霍金那样越来越重,怕是好不了啦。唉. . .,唉. . .,我知道. . .”
我没有睡着,只是一动不动地闭着眼。儿子的两声哀叹扎进我的心里。男人流泪不会是因为自己可怜自己,而是因为别人怜悯自己。儿子大概看到了几颗滑下我的眼角的泪,赶紧收住话音,拉着阿珠悄悄走出房间,关上了房门。
阿珠的变化从那时候开始了。难道客观上不是儿子促成的?他在生意场上有一套,人情世故上却还幼稚。他无意挥洒出的对亲人的绝望情绪,实际是在告诉阿珠,在这个毫无反馈功能的病人面前,你的行为只有交给良心来衡量了。然而良心的价钱几何?漂亮的阿珠的作为,是儿子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她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和时间来证明,熟悉了厚待她环境之后,在“凭良心办事”的考验中她是如何地不过关。
自那以后,当儿子的宝马冲出车库,向苏州奔去,这栋幽静的房子就慢慢开始不安宁了,我照样只是从耳朵里和皮肤上感觉出来。那双布底鞋换成了更舒适的绒拖鞋,走在硬木地板上“巴塔,巴塔”地响,这响声光顾我床前的次数越来越少,大多数时间是在厨房和客厅里游荡。打手机的声音和电视节目的声音此消彼起。我不愿意刺探她在手机中谈话的内容,但我又怎么拒绝得了那无所畏惧冲进耳鼓膜的音波呢。 从那里,我知道了她的男朋友在上海一家超市工作,我知道她邀请他过来玩,我知道她称赞这里好得他会想象不到。随之而来的是门铃声常常在日间响起,我深夜醒来会有阿珠俩人的嘻笑打闹声从儿子的卧室里传来,仿佛这座近两千万的房屋已经易主。
客厅里的打笑声停了,阿珠走进来给我换尿布。她揭开被子,把我翻到一边,“唰”地撕下旧的,紧接着电话铃响了,她丢下我急忙往客厅跑去,就像丢下一个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她在电话上那笑两声说几句,又说两句笑几声的模式,一定又是和她家乡的闺蜜聊上了,这需要长长的等待。我知道此时我只是一个东西,至少是一个慢慢变成东西的东西。可恨的是我的脑子还很活跃,把我这个僵尸般伏在床上的躯体想象成一只剥了皮的青蛙,就像那只我时常梦见的,初中课堂里的青蛙。那是生物课的肖老师带到课堂上来的,说是要作个试验,让大家了解肌肉对电击的反应。她要两个同学上讲台来,一个抓住青蛙的脚,一个用电极触它,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肌肉的反应。我突然站起来,说,把青蛙皮剥了才看得见肌肉。肖老师优雅的脸上现出了难色,轻声说,那谁来剥皮呢?后来我知道,这一节课的大纲要求展示的是一只“活的,剥了皮的青蛙”,肖老师厌恶血腥,想用一只囫囵的青蛙作了实验拉倒。全班人把眼光转向我,看着那眼光,让我去杀人大概也会干。我大步走向讲台,像作七步诗的曹植,很快回忆起了在菜市场围观到的,卖青蛙肉的小贩的手法,心中有了青蛙剥皮的步骤。要一把刀,我向着肖老师说,有人很快递上一把铅笔刀。我围着青蛙的两只后掌割了一圈,拟出皮肤的头,捏着那点皮顺势一拉,青蛙皮就像一件紧身衣从青蛙身体上脱下来。我听见“哇”的一声从同学的座位上传过来,像排练过的齐唱,令我很舒服。我立即转过头去,注意到她也睁着一双惊异的大眼睛看着我,她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从来不正眼看我。我又回过头望着肖老师,想从她那里得到一句赞扬。她的表情很复杂,当时没有看懂,但是今天却很明白。她回答我说,你回到座位上去吧,我们开始试验。谁会想到当年那强悍的屠蛙人,今天也会像一只剥了皮的青蛙,无助地躺在这里。
我感觉到皮肤有嘁嘁嚓嚓的摩擦声。回过神来,阿珠已飞快地给我换上尿布,盖上被子,离开了房间。接着我闻到有辣椒炒菜的诱人香味,从客厅那边飘过来,这和我没有关系。我的饮食是毫无味道或味道极差的糊状物,他们说是高级材料被高级破壁养生机处理过的食品,大多数时间我对它们毫无胃口。我只躺在这里,没有任何动作,没有能量消耗,脑筋转动所消耗的能量微乎其微。阿珠给我喂水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这样换尿布的次数就会减少。说实话,我的下部身体对尿布中的内容物一天天在失去敏感性。
我在无聊中慢慢地睡去,又从迷糊的睡中醒来,慢慢地无聊,每天如此,周而复始。醒着的大部分时间,我的脑子里是一团五彩的浆糊,无目的地流来流去。也有很少的时间,脑子很警觉,转动得飞快,例如现在。我听到门铃声,接着听见阿珠急忙去打开了门,门里门外的小声对话听不清。阿珠进了我的房间,没有到床前来,接着是和大壁橱有关的复杂的响声,最后我听到大纸箱在地下滑动的声音,经过我的床头出了房门,房门关上了。我想知道那纸箱里是什么东西,除了用劲地回想,别无他法。我记得那个可以装进四五个人的壁橱里,只有我的一点衣服,其余地方都空着。接下来,我听到刚才的一系列音响重复了三四次,最后一次大概房门没来得及关,我听见阿珠和一个男人的对话。
“都是中号的?”男人。
“一个屁股要几个号?”阿珠说着走过来关我的房门。
尿布。他们把一箱一箱的尿不湿搬出我的屋子。不用问谁,我的这点脑子还是可以猜得出来他们在搞什么。我记得阿珠刚来时,儿子给她交代,不管弄脏没有,两个钟头要检查一次尿布,湿了马上换。他按这个数量定购的尿不湿,每月自动到货一次。我拼命想回忆阿珠最近给我换尿布的次数,天亮着的时候两次,黑着的时候一次,除非睡着了也给我换。照这样每个月会多出多少尿不湿啊?
不知过了多少天,儿子回来了。如往常一样,关上我的房门,丢下提包,拧开床头的落地灯,揭开被子,仔细查看我的尾椎和脊背,这大概是他监察阿珠怎样对待我的秘密武器。他怎么会查出点什么呢?阿珠为他的出现几天前把什么都安排妥当了。我摊在床上以来,第一次费尽了力气想和他说句话,就想说四个字,“安监控器”。我费足了劲,颤颤地张开嘴,还没有达到正确的嘴型,便又颤颤地闭了回去,声音出不来。儿子打开房门,喊:
“阿珠,来看看我爸想说什么啊!”
阿珠跑到我的床前,一副诚恳得让人心要化掉的神情看着我。我什么也不想说。儿子对着她学我刚才的四个口型。
“是不是说'灯光太亮'?他不喜欢太多的光。”
儿子半信半疑地关了床头的灯,过来坐在床沿,握着我的手,大概想启发我再说。我已经没有兴趣再尝试,因为我知道了,现在的我,想和说的差距有多大。说句话就像要把我这一生再过一次那样艰难。半睡眠状态,一点点微弱的思想带着我在冥冥中飘浮,倒像很舒服。
我又想起几十年前起那次终身难忘的批斗会。肖老师和一帮牛鬼蛇神被拉上台去陪走资派挨斗,她的罪名是叛徒老婆。肖老师的丈夫是省里一位知名作家,被揭出是叛徒,肖老师一反她温柔的常态,倾其所能地为丈夫辩护,冲撞并惹怒了造反派。
“肖慧茗没有戴牌,谁去给她戴上?”一位主持会的头,拎着一块厚重的纸板糊成的黑牌走过来,望着我们这些初一的学生,大家都不自主地从原地后退了半步。我看了同班同学一眼,都是那种畏惧又无可适从的神色,使我讨厌。我一把夺过牌子,转身便往台上走,像那次剥青蛙皮一样。肖老师低头站在那里,不看我,也不反抗。牌子是用一根塑料电线弯成的套圈吊着,当我把那套圈往肖老师的头颈上放时,我看见她的脖子那样洁白,那样柔和,下意识地把她外衣厚厚的衣领翻过来,垫在塑料电线下面。肖老师这时候转过眼睛,看了我一眼。她头发凌乱,面色憔悴,但掩不住她的秀美,她的眼神里有一种温和,我不敢直视,低着头默默走下台去。
以后的一年一年,我一直没有去见过肖老师,不知道怕什么,是不是因为她捏着我的灵魂?好多年后的一天,我去了肖老师家,是因为听同学说她摔跤跌坏了股骨。我走进她家,见她坐在轮椅上,还是像在讲台上那样优雅,安详地微笑着,精致的脸庞已爬上了皱纹。我控制不住,扑通一声跪下,头埋在她的脚前,体验那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她先生把我拉起来,推我坐到沙发上。是指责还是安慰我已记不清,但清楚地记得他给我讲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故事。
那是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1971年领导的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初衷是用来验证人性中那些不自主的恶行。参加实验的都是身心正常的中产阶级出生的大学生,他们通过掷硬币的方法,随机地被分派为监狱中的囚犯和看守。随着实验的进行,两组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不自主地随着自己的角色发生了改变。囚犯发生了反抗看守的暴动,而看守则动用真暴力来镇压实际并无罪的囚犯,以致实验的局面完全失控而停止。这个实验如此有名,对它的解释和领悟也五花八门。自此以后,我常常想,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在失去个人和社会道德的巡察,有意无意地进入某种社会角色时,人的邪恶行为会走多远。过去我会因它会想起剥青蛙皮,挂黑牌,现在又会因它想起阿珠和她相好在儿子卧室里的笑声,装尿不湿的纸箱摩擦地板的声音。
“其实,肖老师说你是个善良的孩子,她一直记得那衣领。”听到作家这话,我的鼻子酸得钻心,眼眶里的泪再也噙不住。
不知是营养物的作用,还是我没有老到该死的程度,我感到那些把我身体绑得紧紧的筋和肌肉慢慢地有点松动了。我的手臂可以在被子里移一移,下肢可以缓慢地弯一弯来减少一点麻木的感觉。儿子看到我这点进展,现出了幼年曾有过的的那种朴质的欢欣,他是真心爱我的。遵照医生的建议,他找来一位康复治疗师,每周三次上门理疗。“医生说我爸两三个月后有可能会说话写字。”他激动地对阿珠说。
我康复的进展是那样的缓慢,像盯着钟上的时针看它运动,但是那时针确实是在走。从阿珠那里,我又感到了她初来几个星期的那种关照,伴随着的却是一种沉闷压抑的气氛。再没有辣椒炒菜的香味从客厅飘来,再没有门铃声在日间响起,再没有嬉笑从那边的卧室里传来。我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喜欢嬉笑和辣椒香,但是憎恨裹在里面的邪恶。随着康复的进展,我这种想法可能会有在这栋房子里表达出来的一天了。
儿子这次回来时,坐在我的床沿上写什么东西。我吃力地伸出食指,指着他的笔。他猛然领悟过来,“阿珠,快拿支铅笔和一块硬纸板来,我爸想写字!”
阿珠没有来,也没有应声。儿子起身去阿珠的屋子,叽叽咕咕好一阵,又来到我的床前,弯下身子对我说,“阿珠要走,在收拾行李了。”说完转身又去了阿珠的屋子。又是好一阵,阿珠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只铅笔和一块雪白的硬纸板,放在我的右手边。我思量是不是儿子要她为我做最后一件事。本想要只笔和纸来试一试手的功能,这时我改变了主意。我让阿珠帮我拿住铅笔。我的指头捏不住,只能把笔握在掌中,像握一把刀,靠手腕和手臂的微小运动,在纸板上画出笔迹。我尽最大努力,那一横,一竖,一点,一撇,超乎想象地难于控制,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耐心,慢慢地试着。我这苍老而幼稚的动作,定会是使看的人磨心地难忍,阿珠站着看了一会儿,又回她屋里去继续收拾她的东西。我专注又艰难地弄了好长一阵,完成了我的心愿。阿珠过来了,站在那里,低头看着我,不讲话。我用手掌把纸板往她的方向推,她大概明白我的意思,费了很大劲,连看带猜,念出了纸板上的那些字。对,那正是我要写的:
“不要走吧,那些蠢事我以前也做过。”